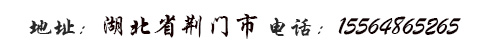付秀莹写尽天下人的心事
|
北京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在哪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 点击上方“文艺报”,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作家 付秀莹 “ 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拥有怎样的人生?我喜欢揣摩他们的内心,我想读懂他们的心事。我想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里,在我的笔下,同他们一道,再活一遍。 创作谈 写尽天下人的心事 文 付秀莹 这么多年了,在一个人的命运中辗转难安的时候,总是私心里暗自庆幸。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摔了这么多的跟头,孤单有时,绝望有时,哀伤有时,虚无有时。好在,一直都没有被磨蚀和损伤的,是对于生活的那份好奇心。 我自认是一个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在菜场里挤来挤去,挑挑拣拣。食物的香气在空气里流荡。小贩的叫卖声沙哑悠长。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哭了。有人在跟卖菜的妇人说话,也不知道是斗嘴,还是调情。我在嘈杂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内心里充满了安宁,还有欢喜。 大约,连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对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究竟怀着怎样浓厚的兴趣。地铁上那个神情忧郁的男人,那个圆润安静的姑娘,那个穿着高跟黑丝的长发女子,艳丽的妆容掩饰不了一身的风尘。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拥有怎样的人生?我喜欢揣摩他们的内心,我想读懂他们的心事。我想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里,在我的笔下,同他们一道,再活一遍。你相信吗?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迎面或许会走来一个人,你似曾相识。他可能在你的小说里出现过,在你的虚构里,他们过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之外,神秘邈远,充满想象。你忍不住看了他一眼,终于擦肩而过。你认识他,而他不认识你。你微微笑了。抬头看天,装作看一只飞鸟掠过。这是一个小说家隐秘而天真的快乐。 《无衣令》中的小让,之所以令我的老同事们牵挂,是因为,这故事的背景设置,是报社。为此,我原来报社的老同事们,纷纷向我索书。我猜测他们的心事,大约不外两种:一是担心。担心自己被写进去,被不小心戳破了心事;二是好奇。看一看里面都写了谁。更有那些好奇心重的,想看一看,是不是其中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对于女作家,这种好奇心大约会更强烈罢。这是性别歧视呢,还是性别优势? 当然也不可否认,我所有的作品里,几乎都有我的影子。譬如说,《红了樱桃》里,樱桃的心事,何尝不是我的心事呢?偌大的京城,樱桃何止成千上万?从乡村到城市,精神的迁徙,心灵的动荡,情感的颠沛流离,在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的强硬碾压下,樱桃们几乎无路可走。他们在北京的夜色里彷徨歧路,不知所往,满怀着无限心事,说也说不得。还有《醉太平》里的老费,中年男人的非典型生活,中国文人的各种不着边际的白日梦,小梦想小野心小痴念小纠结,在内心里蠢蠢欲动,欲罢不能,却终至无可如何。个人总是被身处的时代所劫持。待要挣扎一番,不料竟还是困在局中,不得自在了。 《出走》里的男主角陈皮,忽然有一天,想从平淡乏味的日常中逃逸出来。对妻子的不满,对庸常麻木的婚姻生活的厌倦,对年轻女同事的想象和绮念,对远方和未知的期待和寻找……陈皮满怀壮志,一早离家出走了。然而,在自己家附近闲逛了大半日,黄昏时分,终于又重新回到家里,回到妻儿身边,回到他一直怨恨的生活之中。这样的结局,大约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吧。谁敢说,这个叫作陈皮的男人的心事,不是我们自己的心事呢? 还有《尖叫》里那个女主人公今丽,在婚姻巨大的滑行惯性中昏昏欲睡,那一声尖叫,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把貌似完美无缺的生活,顷刻间打碎了。人性如易碎的瓷器,小心翼翼抱着,还是无妨的,这世上,不是情非得已,谁有勇气用力一摔呢。 《刹那》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内心逃亡和回归。曲折幽微处,亦是小说家笔力纵横处。虽然看似平静,内里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东西在,令人不禁脊背上渐渐生出寒意。人生不易。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深究的。 或许是审美偏好的缘故,喜欢旧的东西。旧的人,旧的事,旧的光阴。相较于新,总觉得,旧的事物里有一种悠长的时间的气息,教人信赖,教人内心安宁。如果说小说也有色调的话,《旧院》的色调,应该是淡淡的琥珀色,流年似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旧院里那些男人女人的斑驳心事。父辈祖辈们在人前端凝方正,又熟悉又陌生,我总是想悄悄切开一道缝隙,窥探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心生活。 在《小米开花》里,我其实是想写出一个女孩子的隐秘心事,孤单的、敏感的,仿佛一根战栗的琴弦,脆弱、纤细,轻轻碰触,便铮然有声。那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光历险,懵懂茫然,在青春岁月里阴暗孤僻的隧道中独自摸索,青涩的疼痛,纷乱的时间的飞尘,对世事最初的想象和猜测,天真的执拗和貌似老练的世故……我试着慢慢打开那个小女孩紧闭的内心。没有人知道,那个小小的乡村女孩内心经历过什么。在小说里,她的父母,她的兄嫂,她的诸多亲人,都在她的紧闭的篱笆墙外,谁也不曾真正走近过半步。小说结尾,小米哭了。然而,这泪水不是那泪水。是苦涩还是甜美,除了小米,谁也不会有机会尝到这泪水的滋味。 《灯笼草》里的小灯,心事明明灭灭,似有还无。我喜欢在那些人性的边界处小心翼翼地游走,微妙的、惊险的、战栗的,有一种纠结于毁灭和新生之间的审美的力量,仿佛悬崖上恣意绽放的罂粟花,有多么绝望就有多么美丽。我敢说,小灯的心事,几乎是所有天下女子的心事。只是我无意中代她说出罢了。 小说家是怎样一种人呢?我理想中的小说家,应该是对生活,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充满了热情,还有好奇心。他们既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又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菩萨低眉,冷眼热肠,想试着勘破世道的隐情与人心的秘密。 写尽天下人的心事。这是一个小说家近乎狂妄的野心吧。 ——付秀莹《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自序 《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 付秀莹 花城出版社 年6月 精彩书摘 旧院(节选) 文 付秀莹 我一直没有说我的四姨。怎么说呢,在姥姥家,四姨是一个伤疤,大家小心翼翼,轻易不去碰触。在旧院,四姨是一个忌讳。 如果你对乡村还算熟悉,那一定知道乡村里的戏班子。在乡间,总有人迷恋唱戏,收几个徒弟,吹拉弹唱,排练一番,一个戏班子就诞生了。乡间的习俗,逢丧事,但凡家境过得去的人家,丧主总要请戏班子唱上几天。其间,酒饭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酬金。在当时,算是可观的收入了。然而,当四姨闹着要去学戏的时候,姥姥坚决不依。姥姥的看法,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戏子,更是为朴直本分的庄户人家所不齿。四姨一个好端端的闺女,怎么能够入了这一行。四姨哭,闹,撒泼,绝食。姥姥只是不理。小孩子,示一示威罢了。况且,在这几个女儿中,四姨的孝顺乖巧,向来是出了名的。按照姥姥的盘算,是想把这个四女儿留在身边,养老送终。可是,姥姥再想不到,四姨会喝了农药。当终于救过来的时候,四姨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我要唱戏。姥姥长叹一声,泪流满面。 农闲的时候,晚上,村南老来祥家的矮墙里,就会传来咿咿啊啊的戏声。这是老来祥在教戏。据说,老来祥的父亲是地方上有名的旦角儿,人送绰号小梅兰芳。唱起梅兰芳的段子来,简直出神入化,名动一时。后来,小梅兰芳因情自尽,身后,落下一片唏嘘,人们都说,这是颠倒了,错把戏台当作人间了。论起来,老来祥也算是有家世的了。自小,老来祥就迷恋唱戏。一个男孩子,说话,走路,却全是女儿态度。人家的一句玩笑,就飞红了脸。就连笑,也是兰花手指掩了口,娇羞得很了。为此,村子里的人,尤其是男人们,常常拿他调笑。老来祥一直未娶。谁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呢。公正地讲,老来祥人生得周正,标致倒是标致的。穿了家常的衣服,举手投足,也自有一种倜傥的风姿。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因此,对于老来祥的态度,村人们是含糊的。感叹,也宽容。这样的一个人,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也跟着四姨去学戏。老来祥坐在太师椅上,怀里抱着胡琴,微闭着眼睛,唱一句,四姨学一句。四姨站在地下,拿着姿势,唱到委婉处,看不见的水袖就甩起来,眉目之间,顾盼生情。灯光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一招一式,生动得很。我看得呆了。眼前这个四姨,忽然就陌生了。这个唱戏的四姨,不是我平日里熟悉的四姨了。平日里,四姨是羞涩的,内向,寡言,近于木讷。而且,四姨也算不得好看。四姨的鼻子扁了一些。四姨的脸庞也宽了一些。女孩子,总是瓜子脸,才来得俊俏,我见犹怜。可是,唱戏的四姨,就不一样了。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光彩。真的。后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四姨唱戏的样子。痴迷,沉醉,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水波跳荡,流淌着金子。 四姨天生是块唱戏的材料。扮相甜美,嗓子又好,在台上,只一个亮相,不待开口,台下就轰动了。老来祥微闭双眼,把胡琴拉得如行云流水。四姨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台下霎时风雷一片。我姥姥坐在家里,拣豆子。我姥姥拒绝去看四姨唱戏。可是,她却无法阻挡四姨的声音。四姨的声音像细细的游丝,一点点蜿蜒而来,飞进旧院,飞进姥姥的耳朵里,飞进姥姥的心里。姥姥拣豆子的动作明显慢下来,慢下来,凝住,嘴里骂一句,这死妮子——长长地叹一口气。 流言是慢慢传开的。说是四姨跟老来祥。这怎么可能。村里人都说,按辈分,老来祥当是叔叔辈,虽说早出了五服,可再怎么,人家是水滴滴的黄花闺女,嫩瓜秧一般,老来祥一个老光棍——也有人说,唱戏,能唱出什么好来?戏文里,才子佳人,演惯了,就弄假成真了。有人就唱道,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就笑起来。 那些天,旧院出奇地安静。我姥姥照常下地,忙家务,脸上却是淡淡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自己养的闺女,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她早该想到的。自从唱戏之后,四姨就不一样了。原是说这四姑娘性子木一些,调教一下,也好。可是,谁想得到这一层。其时,老来祥,总有五十岁了吧,或者,四十九,唱了一辈子戏,谙尽了风月——四姑娘又是这样的年纪——怎么就想不到呢。姥姥很知道,一个女人,最不能在这上面有闲话。姥姥家里,旧院,出嫁的,待嫁的,全是女儿家。这种闲话,尤其具有杀伤力。我姥姥坐在院子里,手里的棒子一起一落,把豆秸砸得飒飒响。四姨躲在屋子里,只是沉默。 这个冬天,四姨再没有去唱戏。腊月,四姨出嫁了。嫁到河对岸的一个村子。四姨父,我是见过一面的。个子矮一些,跟高挑的四姨站在一起,尤其显得矮小。人却老实。姥姥说,人老实,这是顶要紧的一条。出嫁那天,是腊月初九。雪后初晴,格外地冷。四姨穿着大红的喜袄,勾了头,坐在炕上。响器班子站在院子里,卖力地吹打。新女婿早被人涂了一脸的黑鞋油,像包公,嘿嘿笑着,只露出白的牙齿。陪送的人再三劝道,走吧——不早了,路远。四姨这才慢慢站起来。院子里,唢呐更热烈了。四姨推着披红挂绿的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出旧院。四姨化着严妆,那一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四姨在想什么呢?戏里戏外,天上人间。四姨再不会想到,这一点小小的挫折,跟后来漫长的人生磨难相比,不值一提。真的,不值一提。 后来,我总是想起四姨唱戏的样子。那是她生命中盛开的花朵,娇娆,芬芳,迷人,也危险。作为一个女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隐隐地认识到,美好的,总是短暂的。我开始害怕看姑娘们出嫁。而在此前,我是那么热衷于看热闹,挤在人群里,心神激荡。相比之下,我喜欢那些绣鞋垫的日子。描画着,憧憬着,然而,都在远处。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旧院又平静下来。我姥姥立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鞭炮的碎屑,空气里还有硫黄的刺鼻的味道,雪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一道道车辙,交错着,纠结着,终是出了旧院。姥姥把胸中的一口气慢慢吐出来,长长的,在眼前缠成一团白雾,也就一点一点散了。 姥爷是照常地无所事事。田地里,难得见他的影子。他多是扛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子里消磨光阴。家里的事情,他懒得管。他只知道,即便天塌下来,有姥姥顶着。他放心得很。经了四姨的事,姥姥的脾气渐渐大了。这么多年,她是受够了。男人,都是遮风挡雨的大树,可是,在旧院,姥爷却先自缩起来,把她这柔软的性子,生生地百炼成钢。是谁说的,一个家里,如果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也就不是女人了。这是真的。先前,姥姥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女子,在娘家,虽小门小户,却也是娇养得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了人,不待开口,先自飞红了脸。说起这些,谁会相信呢。姥姥大闹一场。她坐在炕上,哭,只觉得委屈得不行。四姑娘的事,要不是姥姥做事果决,怎么能够这么干净爽利。是她,把这杯苦酒,自斟自饮了,还不露一丝痕迹。她知道,这种事,在女方,最是张扬不得。尤其是,旧院一大群女儿家,人们的嘴巴不济,张口闭口,不经意间,就伤了这个,带了那个。她知道其中的厉害。她必得把这一口气,咽回肚子里。也有好事的人来探口气,既然事已至此,不如顺水推舟——老来祥人还不错。姥姥心里冷笑一声,怎么可能。不要说年纪辈分不对,把一对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皮子底下,这后半生,可怎么做人?姥姥脸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托了人,把男方家底都一一摸清,自忖闺女过去受不了委屈,就下了决心。这其中的坎坷煎熬,能跟谁讲?姥姥坐在炕上,哭道,聘了这几个闺女,哪一个不是我,一应的琐事揽下来,日夜撑着——要他这个男人做什么? 后来,我常想,可能是从那一回,姥姥才铁了心要招一个上门女婿,以壮门户。 往期精选 1.铁凝: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 2.来吧!听莫言读诗说戏 3.迟子建:最是沧桑起风情 4.世界那么大,我要找到你 5.金波:好一个萧萍 6.这是一袋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薯片,里面有诗的味道 7.香港回归20周年:一次次呼唤你,我的年 8.异常胆小的余华,叙述死亡时却毫无恐惧之感 编辑:樊金凤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文艺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每周一、三、五出版。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年9月25日,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 文艺报长按识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xw/8053.html
- 上一篇文章: 小路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