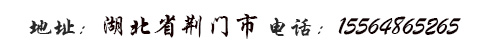野神我腿怎么这么短
|
/第十八届叶圣陶杯初赛一等奖食用提示:-小说总长字,建议备好薯片可乐,以供下饭之用-因为赛级而作,难免有伪枉矫饰之嫌,和平时文风略有不同,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意图,权当写着玩玩,看着玩玩:)以上0“你说风来给我听卷起灵魂飞到不见一阵风吹过金黄色的树叶被隐藏这样的这样的黄昏里我好像一片树叶你也好像一片树叶”——《德斯特旧日》①1 我的名字是季洵。 德斯特②平原上的一位神明给了我这个姓名。我唤她世子,而事实上,德斯特的其他生民更愿意称她为野神。 她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神明。 她的过往,我无从知晓;她的一切都好似黎明山谷中游动的薄雾,冷湿而捉摸不定。而隔了一层时间与岁月共同淘澄的金沙后,记忆里的她却好像变成了温暖而可触碰的。她似与我无关,她的身份,她的特殊性都让这种论断无可指摘,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 事到如今,我已然忘记了大部分关于她的事情,就连她的名字,也要费力回忆很久才能想起,更不用提有关她的种种传说。然而每一个清晨,当我睁开眼睛,任凭第一束阳光流淌进我的世界时,原本恍若隔世的、理应远去的一切却又会清晰地上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些都不是假的,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说来也许会让你惊讶,但实际上,健忘的我,在这些年的每一天都无法忘记她的模样。 我们拥有一模一样的容颜。 2所谓野神,平原之神,原野之神,德斯特唯一的神明,拥有毁天灭地的能力,也拥有赐予万物生机的力量。生民畏惧着神祗,又真切地信仰着神祗,故此,在德斯特这片不大的平原上,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她的印迹:为她而建的神庙不计其数,有关她的传说口耳相传,甚至于为她而庆祝的节日,一月里都要过上两三个。对于她的存在,众生是这样深信不移,就好像是真的亲眼见证过一样——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生灵见过她的样子,或者说,能记住她的样子,除了我,和一个独特的种群。 孩子。 “谁说德斯特的生民都是人类?” 3位于奥利弗③帝国中南部的德斯特平原,既不广阔,亦不富饶。动物是这里的主人,我也是动物。 ——人是万千动物中的一种,而单单这一种,又能造就出万千的的生命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而生命又怎不是如此? 所以那些孩子,我是指,所有动物的幼崽时期的统称。当他们处在那样的一个发育阶段中时,野神是可以被看见的,不仅可以看见,而且可以被感知,能够触碰。只是这个阶段的生灵大多尚未学会表情达意,故而成年生民们所获得的关于野神的信息,便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为具象的关于野神的描述,均出自于尚未开智的幼崽们之口,而那些奇异的、荒诞不经的证言,也会被当做一手的资料,庄重地载入德斯特神史的史录中。 若不是成年之后,生民们头脑中有关于野神的记忆会被野神自己(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抹除的一干二净,对其的感知能力也被削弱至消失,德斯特的生灵们也不至于从模糊不清的无忌证言中,拼凑这位神明的冰山一角:活泼,生动,容易亲近;又或许是情绪起伏不定,喜怒无常...... 没有谁知道野神这样做的用意:祂无私的予每一个处在幼年阶段的生灵以恩泽,却又在他们刚刚脱离幼年这种需要索取的、脆弱的生命阶段时,就残忍地抹杀掉关于祂的一切记忆,徒留一个模糊的点,伴随着单向的、无可逆转的时间的流逝,逐渐朦胧。 ...... 而这些都是很渺远的事情了。我说过,若不是那些欢愉与痛苦太过真实,真实到几乎到了切肤的程度,现在的我就断然不会认定这一切真的曾经发生,而是宁可把我自己投放进某个有资质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早些时候,我还不能说服自己,无法理清那横亘在如今我的生活与过往的种种之间的那条线,因此写下了许多——那或许是我所留下的唯一能够记述我挣扎过的痕迹;然而也许是时过境迁,如今的我却觉得,那条线也许不必被牵扯的那般分明了——毕竟那线如同野神一样(哎,还是唤她为世子更为习惯。),本身就像沼沼的水雾一般神秘莫测,硬要与它纠缠,反而会两败俱伤:失魂落魄地看它从你指缝间溜走。直到现在,我还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这些。 然而一旦被裹挟入记忆的洪流,任谁也难以轻易从其中抽离。思前想后,我便也不愿再多加剖析,仅附上一段那时我留下的文字,让故事从这里讲起吧;以终为始,也许能让人体会更深,不是吗? 那关于我自己的,未曾容他人拜访过的神秘境遇。 “那条小溪依旧匆遽地流而你已经随它远去我知道你把声音留在了一层一层杂花生树来搪塞我为你存在过的唯一证据那些说过的没说的犹豫的急切的留作树上的果实好让我百无聊赖也有清晰的昨日可回忆”——《德斯特旧日》故事,从这里开始...... 4什么活动的举办是德斯特平原最为喧腾的时候? 每月几次的祭祷已经足够让德斯特的生民们陷入狂欢:大家祝祷、欢聚、享受野神所赐予一切;但事实上,每年德斯特最为重要、也是规模最为宏大的节日,还是一年一度的平原祭。 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回看,我依然无法理解当时的野神——世子的心理。这位站在我身边的神祗,用她一贯清楚的眼神注视着平原上一切生灵的熙熙攘攘:祝祷、献祭、感谢她一年所赐予的风调雨顺。 而这一切都是只为她的。 事实上,当我生长到能将这样盛大的活动条理清晰地完整记述下来时,早已经过了德斯特广义意义上的幼崽时期,可世子却仍旧能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让我心惊,肃然起敬中,也夹杂着一种自己似乎是天选之人的庆幸——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可以?而关于脱离幼年时期仍旧能看见世子的这件事,我并没有向别人说出。 世子是神,尽管她女性化的体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她的威严(至少在我心里是如此),她与我一模一样的外貌,也曾让当时的我产生过疑惑——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相似就越来越明显而昭然若揭。关于这件事,我从没有向她询问过,而是对她付出了绝对的信任,绝对的信仰,也是绝对的依赖,甚至没有理由。我信任她的给予,信任她的授意——在其他生灵眼中这叫做神谕。 “天降福音。” 这是德斯特的生民们祝祷时最愿意说的一句话。我想,这句不长的话语似有魔力,荡涤心灵的同时,又能给自己的心灵寻一处慰藉之所安身。也许,祝祷的意义亦是如此,取悦野神是次,使自己心安是真——这是某次当我偷眼去看世子在这种场合中似笑非笑的模糊嘴角时所得出的结论,非我僭越,我想神明之心亦如明镜。 5平原祭总是结束于黄昏。 我仍能记得那时的天色。一望无尽头的平原上,一轮红日正在缓缓西沉。它发出的光被散射成不同的颜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绀色,也不是刺眼的明黄,那种困倦的、怠惰的色调,像是被随手打翻的调色盘里的油彩,交织融合,愈来愈深,逐渐变得难以分明,最后凝固成夜晚时分德斯特平原每一个的湖泊一样的深黑。 今天的月亮很好,是满月,银白的月光洒满整片山峦。我陪伴着鹿小七离开山顶,走在通往家的路上——年年如此。它看着我身旁的世子,蹄子撞击地面发出有规律的敲击声,它很开心。 鹿小七,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鹿幼崽,一只不会说话的、心智不健全的哑巴小鹿,一只除了季洵,再也没有别的朋友为伴、亲人为伍的小鹿。 我手里提着篮子——我记得自己是要去采煮蘑菇汤用的蘑菇。德斯特平原上的蘑菇很好找,因为它们是会发光的。想要辨认是否是毒蘑菇也很简单,因为只有毒蘑菇是发红光的,但鹿小七不会辨认,因此我每次总是要多加提醒;好在它虽然不甚聪明,好奇心亦不甚旺盛,除了青草,对蘑菇并不感兴趣。 已至深夜,喧嚣了一日的德斯特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盛大的喧闹总要在过去之后,当身体再次被投入宁静中时,它的回音才会姗姗来迟,敲打在你心里,勾连出更多纷繁复杂的心绪,让孤独被此刻的寂静无限放大。幼年时的我断然不会这样觉得,而长大的我将这种情绪看作是时间给予我的馈赠,毕竟,这种情绪除了能够帮我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外,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危害。 只是鹿小七从来不会有这种奇怪的负担。从我第一次见到它的眼睛,到最后一次注视它的眼睛,都是一样的天真,清澈,深黑似如镜的湖泊,而这又是后话了。 6如今回想起来,我的确能够在世子的只言片语中,在她某些离奇古怪,为当时的我所不解的举动中,管窥到那些她早就想告诉我的话——如果我能够再聪明一些、再敏锐一些,是不是当她离开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坦然;更早地摆脱那种沉重与悲伤呢?但若是如此,我也必然能够预测到鹿小七死亡的必然,而我又会因此更早地陷入失去朋友的悲伤。所以再次回想起来,我也只能坦然地说一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和世子谈话,很需要精力,因为和她说话总像在猜谜;每长一岁,这种感受就要增加好多,也是这种时候,我才能更加清晰感受得到,褪去身份、名称的限定,真正的“神”与我之间,到底相差几何。 所以当那年的我向她抛出那个问题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惊讶。虽然这种惊讶像被微风吹皱了的湖面,仅仅停留了一瞬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也足够难得——像是听见了万古的冰河碎裂的声音,那是万物复苏的临界点,生命走进新纪元的开始;这种隐秘的不安与狂热的欣喜让我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唇,迟钝的心弦已被拨响,愚钝如我,也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有些东西已然发生了变化。 “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自由?” 7“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自由?” 短暂的沉默过后,是她一如既往不咸不淡的声音。短短的一句话,被她翻来覆去重复了好多遍。 “那么你告诉我。” “洵,是什么让你感受到了自由?” 是什么让我感受到了自由?我愣住了。但很意外,充斥在我心里的,没有对神不敬后的惶恐,有的只是一些更抽象、更虚无缥缈的东西,足够丰富,也足够让我陷入亲手为自己设下的迷乱—— 我想到初春德斯特上空掠过的白鸽,它的轻盈美丽足以在我心里成为风的具象:来去自由,无所拘束;我想到盛夏吹拂过德斯特平原的风,风里裹挟着鼠尾草淡淡的苦涩与七里香浓郁的甜蜜;我想到在混有鼠尾草与七里香的青草里打滚的鹿小七,它日趋健硕的身体下蕴藏着无限蓬勃,似一条奔涌不息、澎湃的热河;我想起曾用那样模糊不明的眼神凝视过鹿小七的世子——她崇高、她拥有我无可比拟的力量;她教人难以捉摸,她的身上有太多我无从知晓的秘密;她来去不定,她恣肆自由...... 但,却又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心里,密密麻麻地生出尖刺,叫嚣着抗议,他们并不满意这个答案...... 明明还有什么,会比神明的指引更可贵...... “您是自由本身?”我斟酌着,谨慎地遣词造句。 “我?我不是。” 我觉得她笑了。 “当自由这个词被创造出来时,创造它的人就已被永久地被自己禁锢,但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最为珍贵的馈赠,它的重量足以同他所追寻之物等同。” “哎?” “你长大了,季洵。”她忽然转过了身朝向我。 “您要离开我了吗?”我微征,不明白这种莫名的失落是怎么回事。 “不,不是这样,至少暂时还不是。”她微微摇头,似要动作,“我只是在感慨,你可以成长地这么快,真是....令我惊讶。” 一种温暖从我的心口漫开,顺着与它相连的世子的手,心脏的跳动得以清晰地在耳边响起,砰砰、砰砰。 “跟随它的指引,而不是我,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哎?” “不过,想要得到,你就必然要......” “啊?” “没什么。”她的表情捉摸不定。 “只是顺其自然的命运而已。” ...... 8而当我赶到山顶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直觉向来极强,事实上,自从那天结束与世子没头没脑的谈话之后,尽管我并未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但也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一丝不安。 失去?失去什么?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我头痛万分。野神的蝴蝶给了我动令——那是她联系我的方式,我曾经以为,她也许很喜欢我这个小朋友,才会为我留下这能够追随神迹的信号。 没有声音,周围是死一样的安静。天边有一轮月,是满月,那只赤红的蝴蝶在暗夜的流光里扑朔着翅膀,闪闪烁烁指引出一条道路;翅膀落下的鳞粉是和毒蘑菇一样的颜色,不详的红。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只被灌木缠绕住的残缺的角。 “维维谷离德斯特很远,以前从未有过关于狼人的记载,也许是满月的影响,这个意外……” “不是意外。” 我打破了所有的顾忌,僭越、逾矩。 我看着她的背影,看白色的光一点一点从鹿小七身上升起,汇聚在她的手里——她在为它超度。德斯特的每一个生灵,灵魂都是有颜色的,这颜色只有在死后才能被知晓;同样地,其颜色越纯粹,越代表着那个死去的灵魂拥有最纯洁的本真。 “...你早就预料到了,对吗?” 世子转身,阖眼向我靠近,一步步地,本能的畏惧让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然而,她却走过了我,在与我错肩后站定。“季洵。”她的声音在空气中震荡,“我以为你会明白。” “我没有能力。” “你明明有。” “我有什么?”她的声音仍旧云淡风清,“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也不一定会来;就算你来了,也许你会奋力搏杀,但也无法摆脱失败的事实。”世子垂眸,看最后的白光在手里黯淡,“而它也一样,甚至更加无力。” “但你可以……”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帮你?”她的表情似笑非笑,“你怎么敢这样肯定?” “你怎么敢的?” 一只手在我愣怔的间隙抚上我的心口,在我错愕的目光中,她猛地一推。 视线中的景物不断下坠,所有的一切变得模糊—— 记忆的最后,是一只蝴蝶在风中抖动的翅膀,通身赤红。 9再次醒来是在小木屋里,除了被她庇护,我想不出来第二个关于我从山顶跌落却能大难不死的理由。 我阖眼,感到疲惫万分。靠在木板上,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一只笨笨的小鹿在另一边,小心翼翼地抬起蹄子敲击只有我们才能明白的暗号。顿时,一种酸楚细密地涌上心头。 那只用来与世子联络的赤红蝴蝶也不见了踪影,倒不如说,是自从我醒过来后就再没有见到过世子。整整一个月,我游荡在德斯特的平原上,像个孤魂野鬼。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大家口中的野神,我甚至以为这是由于是我变成了成年人的缘故。若果真如此,成长的代价也太大了,我漫无目的地想,觉得可笑。 我无法理解世子冷眼旁观的原因,这不合情理,故而我只能怀疑这是她能力的问题。我开始怀疑,她是否真的具有德斯特的生灵们口中无可比拟的力量。然而每当顺着这条脉络继续往下想的时候,思维往往会走到死胡同里——她毕竟用她的力量救了我,虽然把我推下山崖的人也是她,但如果没有她我就会死。我承认,我对她确实所知甚少。 我不得不去查访一些从未有人涉足的地方,比方说,神庙的禁地——再虔诚的信徒也不会拜访这里,野神休息安眠的地方。他们对其绝对的崇拜让他们不敢如此僭越。 但是我不——我已不再对她报以狂热的信仰,哪怕她曾是我幼年时完全的信赖与倚仗;我现在只是在寻找,在追逐,甚至是在推翻;我试图用自己所能,去解释那深埋在我内心的迷惑,那日日让我痛苦的根源。 我走访遍了几乎整个德斯特境内的神庙——很遗憾,大多数神庙供奉的神史、雕刻的壁画中都只记载了一些为她歌功颂德的话语,而关于她曾为这片平原降下的神迹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其可信度又颇低(那歌颂太浮夸);她的形象,甚至都未曾被完全还原,公之于众。 行至疲惫时,倚靠在神庙的庙阶前,偶尔我也会想:她真的存在吗?这一切会不会只是我的一场梦?但一想到不会有那么多生灵和我做同一场梦,我必要自己查明这一切时,内心的迷茫与对可能的报应的畏惧便又会烟消云散。 这是一种出于什么心态的追寻呢?仇恨、不甘?平心而论,那夜在山上世子说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让自己和鹿小七全身而退的能力,而她出手相救也不能被视为一种必然——这事毕竟跟她无关,她能好心提醒我一句已是万幸。但她说出那样的话,把我推下山崖却又赐我新生......这扑朔迷离的一切早已交织成一张网把我囿于其中,除非由我亲手解开这个谜底,否则我必不会善罢甘休。 我走进了眼前的神庙。 10这是一座奇怪的神庙,事实上,它通体上下给人带来的感受就是不祥,若不是神庙口刻有的野神象征性的符号铭文,但从内里的陈设看,几乎找不到任何与野神有关的联系。整个建筑被通体漆成红色,不是砖红,是那种发黑的暗红色——这颜色很容易使我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物。而也许正因这不祥的气息太过强烈,整个建筑也较其他神庙更加破败,剥落的砖石,横结的的蛛网上灰尘遍布,恐怕是很久未曾有访客涉足了。 握着从前殿台阶的缝隙中生长出的灯笼草,我向神庙的最深处走去,让手心这带有光亮生物驱散眼前的黑暗。在狭窄的长廊中穿行,我愈来愈感到这座神庙设计的精巧——正逢满月,月光如银色山泉般从墙体上特意预留出的通风空洞中倾泻下来,打在石板上形成一个一个光斑,每个光斑的距离都和谐一致,看上去就像特以为信徒预留的灯盏,错落有致,一直蔓延到很远很远的前方。而与此同时,一种奇怪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脑海,像是女孩子的轻笑,又像是模糊不清的低语,然而传递的信息,却是惊人的相同—— ...... 一只盒子,静静地躺在长廊的尽头。熟悉的铭文昭示了它所被赋予的含义,繁复的纹路盘曲环绕,勾勒出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名词—— 德斯特。 里面会有什么?野神真的在这里吗?我比量了一下我的身量与盒子的关系,觉得不太可能;还是什么神秘的史前生物?亦或是被封印在此处的恶灵? 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像是被它蛊惑了一样,一股莫大的勇气促使我伸出手,打开了它—— 伴随着一只赤红的蝴蝶一起涌出的,是一阵浅淡的香气。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视线的终结,依然是那只蝴蝶翩翩的身姿。 11又一次在熟悉的疲惫与刺痛中醒来,我迷茫地睁眼,不知自己是否依旧身处凡间。然而当我完全清醒,足以看清周围的一切时,眼前的场景却让我惊诧万分: 我重新回到了那座曾经在此坠落的山上! 我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试图确认眼前的一切。满月之夜,月光倾泻于绵延的山峦,勾勒出山脊与山谷间的错落,所有景物如以前无二,就连...... 就连那生民们口中的野神,失踪数月的世子,也像往日一样站在我的身后。 我愣住了,短暂的错愕被利用,那只赤色蝶翩跹而来,停留在我的唇上,带有一种奇怪的魔力,让我无法行动,亦无法发出声音。 “不要说话,让我将你所有的困惑悉数消解。” 12神以信徒的信仰为食。 祂从信徒的信仰中汲取力量,同时又反馈给信徒,但这种反馈是十分微弱的,而对信徒信仰程度之纯粹、自身能力之广博的要求又极为苛刻,换言之,越强大的个体,才能拥有越强大的神明,而强大到足以独自与世界抗衡,神明便又失去了意义。故此,神明的存在便显得有些华而不实。 “原来你说你没有能力,是这个意思......”漫长的一段叙述过后,红蝶翩翩飞去,我来不及活动麻痹的筋骨,更多的问题等待被解决。 “鹿小七看见的,是靠它信仰幻化而出的神明,是我,亦不是我。因它力量的微弱,我确实无力将它拯救。” “神爱世人,也只能是爱世人。只有世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才能换取神明无上的力量,只爱一个人,这无法做到。” “你去了很多我的神庙,其实那都不是我的信徒所建造的。” “哎?” “因为真正的信徒,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啊......” 我想她在我的眼神里读出了难以置信,因为我看到了她的笑容,不是那种模糊的笑,而是那种生动的,能模糊我与她界线的那种笑。 “也许你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幼年的生灵才能看见我。” 13“只有幼年的生物才会付出不假思索的、没有自我的、完全的信赖,这是生存的本能,是最纯真的心灵所奉献的馈赠;而若是成年了,仍旧无法从这种无自我的信赖与依靠中摆脱,这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错误,不仅会让自己会陷入与客观相悖的误区,原本纯粹的信仰也会变得错误,人的灵魂降格为兽——无法独立的灵魂与兽无异。这就是你从未见到一个人类的原因,也是那些成年生灵无法再见到我的原因。” “别那么惊讶,你看到的动物都只是幻像,你指望动物能修出神庙?” 我抬头,对上她的微笑。 “那些感受到自我的召唤的灵魂,早已离开这片平原,去往另一个世界,得以解脱。” “拥有追求自由的意识;拥有寻求意义的渴望;独立而野心勃勃;你不再需要我,你足以符合离开德斯特的所有要求。” “所以,时间到了。” 当我还沉浸在头脑风暴之中时,她已经把手搭上了我的肩膀。记忆中熟悉的感觉慢慢上涌。 “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是从这跳下去的吗?”我看着脚下的山峦起伏,有点牙酸。 她笑而不语。 “等等等等!”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鹿小七......等到了那个世界,我还能再遇见它吗?” 她垂眸,纯黑的瞳反射出无机的色泽。 “原本就缺乏能力的鹿小七,无论信仰与否,不凭借依靠,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想要在另一个更为广博的世界活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以它灵魂的纯粹,足以直接升入天堂,没有必要再去走一遭,你见不到它,也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还有什么话要问吗?季洵?” “再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她的手扣紧了我的肩膀,通往自由的指令已经呼之欲出。 “每一个人看到的神明,都与自己的长相无异。” “因为自己的神明,从来就只有自己。” “恭喜离开德斯特。” 耳边传来呼啸的风声—— 14再次醒来时,身边已经没有山峦,亦没有世子。医院里,被一群七嘴八舌的女孩子围住。他们说,很不幸,我在体操课上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摔下了平衡木,让本该是轻微的擦伤直接演变成了脑震荡。 我困惑地伸出手,手上缠了厚厚的绷带。 如今距这件事情过去已有数年。事到如今,我仍然无法分清那曾经的一切,究竟是真实发生,还是只是我的一场迤逦长梦。毕竟,那感觉太过真实。 我同所有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成长,求学,用一件件小事填满时间的缝隙,只是偶尔吹夜风时还是会愣怔,只是偶尔望向镜子里的自己时,脑海中还是会浮现出她的身影。 大多数时间,那段记忆只是安安静静地蛰伏在脑海中的某一个角落。但也不排除某些时刻、某些诱因的发生—— 望着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再三强调的那个生词,我一阵恍惚。 Destiny.Destiny.Destiny “大家注意,这个词的意思是——”老师拍着黑板,震落了一层粉笔灰在午后的教室里漂浮,“命运——” “来,大家跟我造句,我们都要做命运的主人——” 注:本文所标示的全部地名、书名纯属杜撰。一些叨叨:其实有一些东西囿于客观原因没表达出来。 比如,鹿小七其实是季的另一个人格,“完全单纯”“完全信任”同样“完全无力”,这样的人格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季在潜意识里杀死了自己,也变相地以另外的自己去迎接明日。 关于为什么季从平衡木上摔下变成了脑震荡,其实是她身边的学生所为,是他们将季推了下去,这其实是有预谋的、长久的校园霸凌。这是个社会痛点,处于敏感的边缘,如果写出来,就可以完整地和鹿小七那条线对上,也能和为什么全文那么热衷于从悬崖边做自由落体对上,也可以解释季的转变,但是那样就太阴谋论了(我没敢写,所以走了HE喜大普奔线,还扯了个什么拯救自己),哎,其实根本我就不想搞什么正能量拯救风啊,果然还是向世俗低头了啊。。 本文作者:我腿怎么这么短 作者邮箱: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gj/7818.html
- 上一篇文章: 济民可信虫草菌粉金水宝胶囊礼盒优惠券
- 下一篇文章: 一谷一城长白县新房子镇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