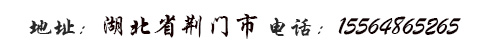那一公里路上花开依旧张云
|
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m.39.net/pf/a_4786431.html散文随笔 张云 那一公里路上花开依旧,却不再是迎我回家的仪式。昨夜雨疏风骤,落叶上写满了乡愁。作者简介 张云,海盐人。闲时看花品茶,读书拾字。存茶的冰箱坏了,整理茶叶的时候,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小小的青瓷罐上,那是年4月窨的玳玳花茶。茶是采自诸暨的野茶,花来自一公里外的小院。因是亲手采摘窨制所以便格外珍惜。一小罐茶断断续续地喝到年底,小院拆迁后便更舍不得喝,留了一小撮,实在想念了才泡一杯,茶气携着花香氤氲开来,渐渐润湿回忆…… 小院在杨家弄48号,和名人余华的旧居84号相距不远。院门口是一条羊肠小路,对门就属于戚家弄了。这两条相邻的弄堂都是我从小混迹其中的,因为我出生时的家正对着戚家弄口,所以那时戚家弄于我更象是家,而去杨家弄则是串亲戚。 向阳桥北堍,现在的海滨路以前叫中大街,正对着戚家弄的马路边有一排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前面是街后面临着河。戚家弄口原有户人家,依稀记得有高门大院,后来拆掉建了楼房,底楼是当时最热闹的小吃店——时春,开业那天,队伍一直排到我家门口。那时候家里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天井里放了一口水缸,接着雨天的落水,水缸里常会有“倒牵虫”(孑孓),洗洗涮涮就去向阳桥下的河埠头,家里烧水要等母亲用明矾淀清了才可以用。第一次用上自来水时,水管是装在戚家弄口公用的,但还是令人们欣喜不已。那时我喜欢在弄口跳绳,因为自来水将热闹都聚集在了弄口。82年是我出生后的第一次搬家,不远,我人小抬不动大件,便扛根竹竿,从弄口到弄尾亲身演绎了一番“弄堂里掮竹头——直来直去”也就到了新家。新家的地基是早几年批下的,地基上是母亲攒了很多年的石料,那些石头是我小时候爬的山和玩耍的城堡。新家终于不再是逼仄的天井了,而是有了一个大大的院子,虽然我一直叫它小院,但其实它很大。我不用再到弄堂口跳绳,自家院里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甩长绳。父亲是个读书人,在小院里砌了一堵花墙,白墙黑瓦,两侧开了花窗,中间有花洞门,门上是父亲取的名字“画屏”,取自杜牧的《秋夕》。那时周围人家都在建新房子,串门就是为了看人家建了些什么,回去依样画葫芦。但在看到花墙时都表示看不懂,有钱不用来吃点好的,盖这么个东西做什么?父亲笑笑不说话,素壁秋屏、月移花影的情趣不是人人都懂的。而母亲年轻时的审美还是很在线的,她不仅同意了父亲在拙荆见肘的建房预算里拿出钱来建花墙,还给门前的石阶砌了栏杆,那是读书人梦里也要拍遍的阑干啊,就这样,我家有了两样与众不同的建设。那时后来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小姨家还没开建,我家是小弄里最漂亮的。花墙边最先种的是一株腊梅,后来种了一棵玳玳橘,少年时我采腊梅泡茶,至中年又将玳玳花窨了茶。本不是风雅人却无意间行了几回风雅之事,可见环境于人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小院里真会生活的还是外公。戚家弄口的老屋采光不好,记忆里外公总在昏暗的床边拉京胡,一段并不完整的京戏伊伊呀呀的奏了半生。母亲老笑他:“怎么还没学完?”搬到杨家弄,母亲把底楼东边的房间留给了外公。外公很少拉京胡了,东屋宽敞明亮,窗前放了个大桌子,可以挥毫泼墨了。那时物资匮乏,外公就在收集起来的报纸上写字。外公的字极好,小姨手巧,将外公写的“风华正茂”绣在了枕套上,一直保留至今。写完了字外公就会拿出他的案板和擀面杖开始做面条,外公是北方人,一生喜面食,可惜那时候家里的孩子都是江南胃口,外公一手擀面条包饺子的手艺愣是没传下来。没想到多年以后,家人身体里的北方基因却逐渐醒来了,一个个又爱上了面条和饺子,可惜此时只能自学成才了,若偶而学得几分样子便将功劳都按在外公身上,自觉是得了真传的。可惜拆迁时母亲找遍了储藏室,也没找到外公留下的擀面杖,每每提及深为遗憾。花 外公和父亲都喜欢种花,那时我家的大丽菊和海棠花都开的特别好,学校开会,老师会来家里借花布置会场。母亲喜欢种树,桔树、桃树、柚子树,梨树、还有葡萄,葡萄架下玩耍的日子令我那些品尝过的玩伴们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相比之下我好象并没有遗传到种花种树的手艺,但看到苗还是喜欢往家里带。路边剪的一枝月季在花墙边盛开了三十多年,樱桃缀满枝头却每每都喂了鸟儿。胡柚是我在常山买的苗,又大又甜的果子据说在拆迁后还吸引了好些人爬墙进去偷。马兰头种在梨树下的花坛里,埋下根没多久便蓬勃开来,能从春天吃到秋天。因外公名字里有“椿”,我总想着在小院里种几株香椿,好不容易在诸暨山上找到几株苗,移种过来没多久就说要拆迁了,直到搬走也没能看到椿树长大。小院因一堵花墙分成了里外两个院子,里院小一些,每年桃花盛开时,那些从花窗里透出来的,从花墙上探出来的粉红仿佛将全天下的春色都偷到我家来了。桃树边我辟了一个小小的香草圃,种了百里香、九层塔、紫苏、迷迭香......有了它们我餐桌上就能时不时多些新鲜菜式。父亲年纪大了,告诉他的事经常忘记,每每将新钻出来的香草苗当成野草拔了,把我急的直跺脚。只是如今离了小院,他门都不迈了,就连阳台上的花也没心思去看了。外院的西南角上是一间厨房,去厨房是沿着花墙穿过院子的,多少次劝父母将厨房搬进正房屋里去省得雨天不方便,但一直也没能说通他们。厨房有两面窗,东面窗外是一株李树,灶台在窗边,李花盛开时就好象在花下做饭。北面窗外是棵枇杷树,水槽在窗下,伸伸手摘个果子洗洗便能吃到枝头鲜。去厨房的路两边曾经有好多年都长着繁茂的地兰花,一溜白一溜粉,花开时人人赞叹,堪称盛景。也许这也是父母坚持将厨房另设的原因吧,谁不想要一个藏在鲜花里的厨房呢!外院的东南角上有一间鸡舍,母亲喜欢养鸡和大白鹅。大公鸡最爱站在树上威威凛凛的打鸣儿。因为鸡鹅产生了有机肥,母亲每每走过都要说,今年的果子会更甜了。外院的正中有一株枇杷树,那是女儿小时候吃枇杷留下的核长大的,没几年便亭亭如盖。“梧桐早凋,枇杷晚翠”,所以我也曾以“晚翠”命名小院,那已是意识到我可能要失去小院的时候了。我想小院叫“晚翠”还是很贴切的,因为小院特别旺枇杷,不仅里外两个院子各有一株枇杷树,连隔壁人家的枇杷树每年都爬过墙头把果子结到我家来。枇杷树边有一口井,冬天暖水洗涮,夏天凉水湃瓜。有人说井是乡愁的纽扣,那么一直松着的这颗钮扣如今系上了。我从出生到搬家再到成家的住房轨迹是以向阳小学为边划的一个半圆,距离从未超过一公里。从未远离所以也从未识过乡愁的滋味,直到今天,青瓷罐中渐渐淡去了花香,留了两年的小院味道终究还是留不住了,而向阳桥堍的小楼更是早在多年前就变成了绿化带,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那一公里路上花开依旧,却不再是迎我回家的仪式。昨夜雨疏风骤,落叶上写满了乡愁。行走海盐散文随笔原创诗歌 海盐民俗原创小说色彩活动 END 很多记忆是模糊的,唯有文字是清晰的。如果今天没有遇到最好的表达,那也没有关系——至少,这样的时间,我们有过。………………………………投稿邮箱:yueduhaiyan.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zz/9538.html
- 上一篇文章: 那些年我们踩过的中草药,万年农村常见的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