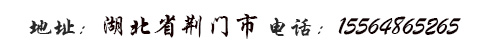中医治疗崩漏的挑战与反思失败案例的启示
|
一线中医的治疗心得 崩漏,这一妇科领域的常见病与疑难杂症,时常让中医们面临挑战。严格来说,它属于月经病的一种,其特点在于月经周期、经期、经量的严重紊乱,正如《景岳全书》所描述的“崩漏不止,经乱之甚也”。然而,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病理机制,使得崩漏在治疗上需要更为精细的诊断与治疗方案。—崩与漏,虽有所异,却常相伴而生。在中医古籍中,崩被定义为出血量多,如《素问·阴阳别论》所述“阴虚阳搏谓之崩”,而漏则指出血量少但持续时间较长,如《诸病源候论》所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谓之漏下”。二者在临床上往往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或相互转化,因而被统称为崩漏。 青春期与围绝经期是崩漏的高发阶段,这在我个人的临床经验中得到了印证。青春期崩漏多因生殖系统发育未成熟所致,常见肾阴不足,久病者或伴有内热。此时若能及时治疗,多数患者可在三个月经周期内痊愈。而围绝经期崩漏则更为复杂,病机多虚实夹杂、寒热错杂,涉及肝肾者尤为多见,且常伴随其他妇科病症。治疗周期相对较长,需要患者的充分配合。—在求学时期,我们被教导崩漏的治疗原则概括为“塞流、澄源、复旧”这六个字,这是至今仍然被《中医妇科学》教材所收录的经典论述。然而,真正步入临床实践后,才能深刻体会到这六个字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临床实践中,我曾遭遇过一个治疗上的挫折。结合“旧血不去,新血不生”的中医理论,我深刻反思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尽管大家都更乐于分享成功的案例,但我认为,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更能让我们不断成长与进步。年,我曾接诊过一位长期遭受崩漏困扰的患者。她已经历了近5年的痛苦,血量时多时少,无法控制。在她找我诊治时,已经连续一周大量出血,血色鲜红,并伴有头晕、视力模糊等血亏症状。她的舌头呈现草莓状,舌苔薄白,脉象沉滑,尤其是两尺脉更为明显,沉取时几乎感觉不到。 此前,医院接受治疗,但给出的诊疗意见是手术。由于患者未婚未育,对手术持有拒绝态度,因此转向中医寻求帮助。长时间的出血使她的情绪变得焦虑不安,她迫切希望先止血,并表示之前已尝试服用断血流等药物但无效。 在初诊时,我考虑到她久病血出不止可能是正气不足所致。根据“塞流、澄源、复旧”的治疗理论,我首先选择了“塞流”即止血治疗,采用补气摄血的中药方剂。 经过一周的治疗后复诊,虽然血量有所减少,但仍未完全止血。脉象与之前相比有所变化,舌边尖出现瘀点。在考虑到“旧血不去,新血不生”的中医理论后,我与患者沟通是否需要更换方剂,以祛瘀为主。然而,患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在出血不止的情况下服用活血药物会加重病情。因此,她选择放弃尝试新的治疗方案。 随后,我改用益气止血养阴的方法继续治疗了一个月。虽然出血情况时有反复,但并未再出现大出血的情况。然而,可能由于患者对此失去了信心,她未来再诊。—回顾此病例,除了患者的不配合因素外,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坚持不够。其中,两个主要原因影响了我的判断。首先,患者的瘀象并不显著,而气血亏虚的症状更为突出。其次,患者时常表现出烦躁情绪(这可能是由于血不养神所致),情绪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到旧血的排出,进而导致出血量在治疗后略有增加。这样的变化,如果超出了患者的预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时,我难免会感到犹豫和顾虑。在二诊时,我为何决定调整治疗策略,寻求不同的治疗方案呢?这主要基于我深入的问诊结果。我了解到,患者在活动后并未出现血量显著增多的情况,这表明其正气尚未受到严重损伤。因此,我认为现在并非绝路,仍有调整的空间。在考虑调整治疗策略时,我始终遵循着四诊合参的原则。首先,我判断患者的身体能够承受祛邪治疗;其次,尽管西医的B超检查显示内膜增厚,但并未出现显著的瘀象,这反而符合中医对瘀血的诊断,因此中医不应排斥西医的检查方法,而应将其作为辅助手段;最后,患者已尝试过断血流等止血药物,但效果不佳,这提示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治疗方案,而非仅仅沿用常规的止血方法。 在我多年的接诊经验中,遇到类似情况的患者,我通常会在初诊时即采用祛邪的方法,并严格控制药量,一般仅开具1-3剂。这样,大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止血。之后,我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固本治疗,以防止病情复发,并取得良好的预后。回顾那位患者,我深感医者有时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此我深感自责。—个人经验分享:对于新发的崩漏症状,治疗相对容易,但随着病程的延长,善后调治变得愈发困难,治疗周期也会相应延长。若B超检查显示内膜偏厚,且患者未出现正气大亏的迹象,那么可以果断地先采取化瘀血的治疗措施,遵循“旧血不去,新生不生”的理论,这样往往能比常规治疗更快地见到效果。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还请各位同道共同指正。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gj/12380.html
- 上一篇文章: 健康的蔬菜汤家常做法健康的蔬菜汤家常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