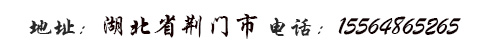新书推介杜怀超苍耳消失或重现
|
北京白癜风怎么办 http://www.sjqbdf.com/ 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植物魂灵 一部野草与大地、大地与人类关系的另类解读之作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首届大观文学奖获奖作品 雷达、杨晓升、夏坚勇联袂推荐 《苍耳:消失或重现》 杜怀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01月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 通过24株植物,了解大地与人类的隐秘关系) 读者对象 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植物、博物爱好者 关键词 植物、大地、散文、苍耳、风物、江南、文学、当代、随笔、杜怀超 编辑推荐 “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站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 《苍耳》中讲述了24种常见的野生植物的故事,但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江南风物志,它将草与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来源自远古,又恒久存在的生命的力量,是如何在人与大地之间存在并蔓延的。 ——策划编辑周莹 内容简介 探寻人与植物的隐秘关联 《苍耳:消失或重现》是青年作家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在这本讲述了苍耳、水烛、打碗碗花、看麦娘、灯笼草、慈姑、蛇莓等24种乡间野草的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却又屡被忽视的植物魂灵。 作者无意以风物志的形式记录这些野草的形态,却从植物自身的特点、生活用途、文化价值、哲学意味、宗教意义以及植物与人、社会的现实关系中,还原了这些野草的本来面目,颠覆了人类对于野草的认知和批判,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野草的文化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史。万物有灵,这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本书给出了人类如何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苍耳:消失或重现》同时也延续了乡村文学的这一文学传统。但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刘亮程等前辈作家不同的是,他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书中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均呈现出一种源自乡村与岁月的风骨和神韵。譬如《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一篇中,他写道:“问荆问荆,拷问的问,荆棘的荆,拷问什么呢?拷问那些充满着坚硬与刺的障碍物,密扎扎地,长在你必经的路上?是一种宣言,还是一种高度,一段段象形的文字?荆,无形与有形,具象与抽象,虚与实……世间有多少事与物都是别样的荆棘?”每个字都力透纸背,引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书中同时附录了插画师弄月之喵的24幅精美植物插画,让人在阅读时,能够感触到植物本身的姿态,同时体悟到人与植物的这种发自内在的,关乎灵魂的隐秘关联。 作者简介 杜怀超男,笔名弋墨,渡白等,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徐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著有长篇系列散文《一个人的农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年版)、《苍耳消失或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长篇散文体小说《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的生存档案》(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扶持项目,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年版)等多部,获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现居苏州。 获奖推荐 《苍耳:消失或重现》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苍耳魂灵。以苍耳悲苦孤寂、坚韧壮丽的一生,写出了它的风骨与神韵,同时思考生与死、社会与人生。文笔优美,笔力遒劲,生动深刻,力透纸背。读来不仅令人动容,亦颇多教益。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颁奖词 朴素的文字散发着野草的芬芳,灵动的叙述却深蕴生活的哲思。草的一生,与人的一生,在大地上重叠,都是大地苍生,都有自己的生存尊严与生存高度。把一棵野草写得如此摇曳生姿,又如此庄严。清新流畅的文字让人读来如饮山涧清泉,蜿蜒涌动的丰厚意蕴却给人带来无尽的思索。散文的轻灵与厚重在作者的笔下得到极完美的结合。 章节目录 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鸭舌草:勿忘初心的漫溯者蛇莓:隐秘草丛的魑魅之影水芹:栖居家园的守望者水绵:水域深处的温暖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萍:无边行走的飘零客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婆婆丁:大地上的异乡者刺儿菜:苟活尘世的疼与痛婆婆纳:诗意的蓝色妖姬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车前草:重轭下的马蹄声灰灰菜:低到尘埃的黑白面孔苘麻:被捆绑的生活或卑微苍耳:消失或重现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 精彩样章 草漫漶 对于野草的思考与写作,源于农具的暂告一段落。农具、野草等这些贴着大地胸膛的事物,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道出。农具的诉说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表述,没有真正地切入大地的疼痛与撕裂,或者说没有真正读懂这些事物背后的真相。我愿意继续探索大地上这逆来顺受的劳作者。但角度的选择或切入口,一度成为我创作的梗阻。偶然,我在书店农作物专柜上看到一本关于刈割杂草的小书,眼前一亮,我找到了野草与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想读懂这世代以土地为命的劳作者,要从杂草出发。这一“杂”字,千钧重量,又如锋利的刀刃,充满疼痛感。她的命名源于生活价值的判断,实则是功利主义作祟。当我翻开此书,读到“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苍耳”“白茅”“艾草”,书中赫然标注可用药除之、利器割之、野火烧之等等,浑身一颤。我似乎应该为杂草说些什么。 回溯人类的文明史,分明就是人类与野草的博弈史。野草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向前。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我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从历史上说,现在我们田野里生长的麦子、稻子等所谓庄稼,最初来源于杂草。庄稼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后的野草。(否则她的宿命就是当下的杂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诞生于世间,应当后于杂草们,这些杂草的先期抵达,可以说是为人类建造大地的温床,建造存活于世的温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看到,人类不仅因为这些杂草获得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而且依靠这些杂草,暖身果腹,走过洪荒,世代延续。远的不说,就拿眼前的杂草,如慈姑、灰灰菜、水芹等,人类至今不是还在餐桌上食用?“人类对慈姑的食用由来已久。南北朝陶弘景便有‘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之可啖’的记载,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也称,慈姑‘煮熟味甘甜,时人以作果子’。慈姑长在浅水中,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耐贮存,是灾荒之地很好的救荒补缺物。”(《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我的旷野里,对于杂草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她们是民间的,属于乡村的自然精灵。土,是杂草的宿命。杂草深谙其中学问,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她们绿色的身影。长在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不到的地方,杂草们都将抵达;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杂草是何时落生何时抽枝整叶的。总而言之,她们在黑暗中潜滋暗长着。我们不要小瞧她们,一旦遇上灾荒或者饥馑岁月,这些杂草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那时候人类的头颅很低,低到杂草的高度,低到与猪马牛羊一样的高度,吃杂草活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与杂草有过关系,甚至有种契约的精神,杂草就是为了人类的到来出现的,并且这种出现以无限的方式遍布,时刻守候着,年复一年,生生死死,荣荣枯枯。 杂草的世界确实让人费解。她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只要给她一点土壤,她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碧绿。你鄙视她蹂躏她糟蹋她,你甚至用锋利的农具,一刀斩草除根。可当你幸灾乐祸不久,杂草再次钻出泥土。泥土在,她的使命就在。人类奈她何?我在写作杂草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人类与杂草的玄秘与匪夷所思。史书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记载着这些杂草的药方、药性等。这已经在呈现杂草与人类肉身的关系。随着写作杂草的学习研究,我发现世间众多的杂草,在药性上,各有千秋,各有个性,治疗神经的、创伤的、心血管的、皮肤的、肝脏的等等,每一种杂草似乎都与人类的肉身对应。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杂草的身上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个发现让我对世界充满神秘的未知感。当人类来到世间,生死不知;可是我们的杂草早已抵达泥土,早就备好生命所需的食粮、住处和治疗肉身的各种草药。而且,杂草的各种药性,居然在暗中与人类自身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回想起来,天地人草等,完全可以看作一个结合紧密的生态系统,人的肉身早就在杂草的重重包围之中。杂草,是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旅行的守望者,生命的守护神。比如益母草,“原来,益母草是一味医治妇科病的草药,有活血、调经等功效”(《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再如苍耳,“《本草纲目》上写道:‘呆耳,亦名胡、常思、苍耳、卷耳、爵耳、猪耳、耳、地葵、羊负来、道人头、进贤菜、喝起草、野茄、缣丝草。(实)甘、温、有小毒。(茎、叶)苦、辛、微寒、有小毒。久疟不愈……眼目昏暗……’直到彼时,人类才明白苍耳居然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生得艰辛,长得丑陋,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待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苍耳:消失或重现》) 人类与草的关系,古人早有清醒的认知。我们从熟知的《诗经》和《楚辞》中可以发现。关于植物的记载,应该说贯穿《诗经》整个内容,花草树木,是《诗经》的原色。也就是说,古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早已看破,天人合一。没有人可以离开自然诗意地生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学会平等相处,尊重万物,我们才将获得生活之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里,诗人居然把肉身寄托在这些芳香四溢、品节高远的植物身上,吃野草,披绿叶,穿行在山川绿林中,与山水拥抱一体,化身自然,与河流、星辰、草木一起朝夕日月。 作品评论 大地盛宴:低处的风景 ——解读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 思不群 文 当年诗人海子自杀后,许多人宣称中国农耕文学也随之终结。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农耕时代也许过去了,但农耕文化、乡村记忆却仍顽强地活在当代文学中。从本质上来说,农耕文明、乡村文学是人类的童年记忆的回响和返照,是人类文明之根。如果回顾一下,不难发现在百年现当代文学中,乡村文学总在不经意间回归人们的视野。从第一代作家鲁迅、周作人等,到沈从文、废名,到八十年代的贾平凹,九十年代的刘亮程,可以发现乡村文学之根始终未断。杜怀超的乡村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但是杜怀超的写作与他的前辈有所不同。在鲁迅那里,乡村只是个很虚的背景,一种渲染与烘托。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村是一种格调与色彩,而且是带有想像空间中的格调与色彩。刘亮程虽然写的是乡村中具体的人与事,但却完全是在说着自己的故事,是经验的独语,那是“一个人的村庄”,他也写驴写狗写马,但是仔细一看,这些都似乎长着人的面孔。杜怀超则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他曾经对乡村农具细细抚摸,在本书中他打量的则是那些野花野草,对这些大地的皮肤,杜怀超给予了少有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cd/6985.html
- 上一篇文章: 提醒一二三四级残疾人都有哪些补贴一
- 下一篇文章: 重磅北乔让野生的念想在舌尖燃起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