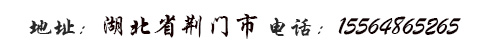李培欣许耘红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
|
指云寺银杏(胡光钰摄) 丽江纳西族聚居地的藏传佛寺园林是丽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物证。在探讨分析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域文脉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对该区域内五大藏传佛寺园林的选址、布局、空间构成、建筑形式、植物配置等进行实地调研,总结其园林环境的地域性特征,对宗教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李培欣,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许耘红,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丽江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境内居住有十余种民族,其中以纳西族人口居多,主要聚居于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1]。该区域为云南省南北宗教交汇点,即“南上汉传佛教与北下藏传佛教及苯教均传至丽江则止”[2]。纳西人对多元宗教文化所采取的“兼容并蓄”态度促成了具有典型民族与地域特色的独特宗教文化景观的形成。图1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空间分布示意图纳藏关系早于吐蕃兴起之前就已建立,纳西族史诗《崇搬图》中曾记载纳、藏为亲兄弟,其历史渊源十分久远[3]。藏传佛教自元末便传入丽域,但直到清朝才先后修建完成福国、玉峰、文峰、指云、普济五大噶举派藏传佛寺,且集中分布于纳西族聚居地(图1)。丽域五大藏传佛寺园林具有典型地域特征,与滇西北及卫藏等其他地区的藏寺园林有明显区别,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形成与丽江地域文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丽江地域文脉构成要素 (一)自然环境 丽江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分布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流经境内的金沙江与两岸山脉共同构成区域山水脉络[4]。与我国大多数山脉的东西走向不同,玉龙雪山延伸出的芝山、普济山、黄山、马鞍山、文笔山等绵延山脉纵贯南北向,将丽域面积最大两个坝区丽江坝与拉市坝分隔开来[5]。此外,该区域为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四季变化不明显,生态环境较好,素有“植物王国”的美誉。 (二)社会文化 纳西族是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东巴文化、藏文化以及以儒释道为载体的汉文化融汇而成的纳西文化,奠定了纳西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6-7]。 1.东巴文化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产生于纳西先民的“泛灵信仰”和巫术文化,形成了支配纳西人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在藏族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纳西族东巴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8]。 2.藏文化 纳藏始于东巴教与苯教之间的密切联系,加之丽江纳西地区曾受制于吐蕃长达百年,藏文化对其社会文化有一定影响。这一历史渊源为元末藏传佛教的传入,以及明清时期在纳西民间形成藏传佛教的普遍信仰和五大藏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 3.汉文化 元、明以后,木氏土司的“窥中原文脉”政策促进了中原汉文化在贵族领主中的流行。清朝“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纳西民间广泛传播,扩散力度胜于藏文化。汉文化促进了纳西族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引发了纳西族重大文化变迁[7]。 纳西人虽居于多元文化交汇点,却始终保持其主体文化意识[8]。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与创新,形成了特有的纳西文化,并将其运用于园林营建等方面,使得五大藏传佛寺园林独具地域特色。 二、丽江藏传佛寺园林的形成与发展 丽江纳西地区统治者木氏土司执政长达五百七十年,掌控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大权[8]。木氏与藏区历代政教关系变化直接影响到丽江五大藏传佛寺园林的形成与发展,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与物证。其园林的形成与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酝酿期:元代以前 元代以前,藏区藏传佛教古老的教派之一噶举派势力在各教派之上,木氏最早于13世纪开始便与其接触,基于“以教安民”的治藏政策,至元朝木氏势力崛起后与其交往甚繁,极为尊崇[9]。这一时期以噶举派为首的藏传佛教流行于木氏土司等贵族领导阶层中,但纳西民间信仰还是以东巴教为主。 (二)转折期:明代 明朝是木氏统治的兴盛时期,明初木氏曾盛情邀请噶举派法王到访丽江,表示与其领导阶层的友好关系[3]。但随着藏区格鲁派的兴起,木氏对待两大教派的态度出现过几次转变,对噶举派在丽江地区的传播也始终持谨慎态度,并规定民间只能信仰,不准随意建寺。随着木氏与噶举派的长久接触,木氏家族逐渐成为噶举派信徒,纳西民间对噶举派的信仰也逐渐扩散,出现大量出家当喇嘛的纳西人,这为后来五大噶举派藏传佛寺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地的修建奠定了信众基础。 (三)生成期:清代 清代,噶举派在藏区政治斗争中失利,其领导阶层逃难丽江,与木氏结盟并进行传教,很快推及纳西民间并形成藏传佛教的普遍信仰。清康熙十八年(年),木氏将家庙福国寺改宗为噶举派喇嘛寺,这一事件作为丽江修建喇嘛寺的开端。清雍正元年(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大力支持丽域陆续修建了十三大喇嘛寺,其中包括集中于丽江纳西族聚居地的玉峰、指云、文峰、普济寺(表1)。清康熙至道光多年间为纳西喇嘛寺的鼎盛时期,乾隆鼎盛时期僧侣多达人,成为丽江信奉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群体[10]。可以说,丽江五大噶举派藏传佛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表1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一览 (四)衰落期:清末至民国年间 “改土归流”结束了木氏在丽江地区的直接统治,逐渐削弱了木氏势力,藏传佛教的政治靠山也逐渐失去,佛寺发展至清末香火逐渐萧条,寺院经济拮据。甚至出现活佛断代的局面。此外,流官在纳西族聚居地实行的汉文化强制普及带来的汉文化冲击,导致纳西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汉文化占主导思想地位,藏传佛教的发展受到抑制,开始走向衰落,从此未再建置新的藏传佛寺[11]。 三、丽江藏传佛寺园林环境特征 (一)选址 丽江五大藏传佛寺均选址于植被茂密、环境优美之地,如今香火旺盛,广为流传许多建寺神话与传说,在卫藏地区也有一定知名度,其选址受宗教、地理等综合因素影响。 建寺之初,木氏土司规定藏寺只能建于坝区周边山上,而不能下到坝区,此规定限制了寺院的选址[12]。然而,藏传佛教本身具有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双重内涵,佛寺的选址以“环山抱水、朝阳避风”为最佳,而丽江坝与拉市坝良好的山水环境为佛寺选址提供了优势。此外,神山崇拜是纳藏共同的信仰观念,认为山为宇宙中心的象征,山林地组成的外部空间则呈现出神圣的特性,佛寺选址于神山更能营造出接近仙境的宗教氛围[13]。因此,丽域纳西族聚居地五大藏寺均选址于山地成为其共性。其中,福国、文峰、玉峰及普济寺分别坐落于丽江坝西侧神山玉龙雪山所延伸出的芝山、普济山、文笔山等绵延山脉东麓,形成纵贯南北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序列,而选址于拉市坝秣度山麓的指云寺占据了拉市海优越的地理环境,且成为该坝区唯一一个藏寺,为周边纳西居民提供了宗教便利(图2)图2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选址分布示意图丽江五大藏传佛寺选址类型均属山林型,又可细分为三类:①选址山间腹地,藏于山间,以幽取胜,如福国寺;②选址山麓,背山面水,交通便利,如指云寺;③选址山腰,居高临下,巧于借景,如玉峰、文峰、普济寺(图3)。图3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选址类型示意图 无论是哪种类型选址,五大寺均西枕高山,东面宽阔栖坝,这样的位置,冬阻西北寒流,夏迎东南凉风,理想的山水格局营造出了良好的小环境。此外,选址均邻近纳西族村落,保证信众基础,方便其前往。五大藏寺占址的优越性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藏寺建造的支持及木氏与噶举派之间的友好关系[14]。 (二)平面布局 主建筑群保留能够满足寺院奉佛、诵经等基本需求的功能建筑,由山门、护法殿(藏语“拉康”)、配殿、正殿(藏语“错钦”)组成(图4)。主建筑群以正殿为中心,沿中轴两侧对称布置配殿,围合形成多进式院落的合院式平面布局,建立起宗教建筑的秩序感。五大佛寺除玉峰寺面积较小为单院外,其余均为前后院式,前院为附园,面积较小,后院为正院,面积最大。除主建筑群规则布局外,寺院僧房、玛尼房、佛塔、本康等宗教附属建筑则根据占地规模、周围环境及宗教欲求不同,依地势灵活布置于主建筑群周围。(三)竖向布置建筑依山势层叠向上沿等高线布置院落,利用踏步将各个院落连接起来,建筑形态层次分明(图4)。依山就势沿台地布置院落的布局方式,既节省建寺成本,又增加空间层次感,营造出不同尺度和氛围的空间,丰富了空间序列变化。此外,依山建寺也能够满足佛教传统的三界空间观要求,佛殿地平置于院落、经堂地平之上,凸显尊贵地位,突出空间集聚中心[15]。图4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建筑布局示意图 (四)建筑风格 丽江五大藏传佛教寺院受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相较于卫藏地区传统藏传佛寺规模小、建筑种类少,建筑群布局形制接近汉地寺院,并吸收借鉴了纳西民居建筑常见做法,藏式特色减弱。 1.建筑造型 丽江五大藏传佛寺建筑融合了中原汉式佛教建筑、纳西传统民居建筑以及藏传佛教建筑元素,形成了具有纳西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建筑形式。 丽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且当地木材资源丰富,因此,五大寺均为汉式传统木构建筑坡屋顶形式,与藏式传统碉房建筑的密梁平顶构架有明显区别[16]。又因丽江地处地震多发带,冬季多西北寒风侵袭,纳西建筑体量一般都不大,且院落狭小。因此,五大寺正殿体量较之藏族碉房建筑略显低矮,但通过竖向上抬高地平以及降低附属建筑高度也突出了正殿的中心地位。五寺正殿多为汉式重檐歇山屋顶,结合了纳西民居中常见的出檐深远的悬山顶、宽大的搏风板及悬鱼装饰物,飞檐翘角,翘角处悬挂风铃,具有浓郁的纳西特色[17]。而福国、指云、文峰寺正殿则是在保持内部基本结构与藏式错钦大殿结构基本一致前提下,在正殿中间二、三层的楼板面开设“回”字形洞口,形成通高两层(或三层)的竖井,其上架设攒尖顶阁楼,顶部镶嵌鎏金莲花宝座,与四面镶嵌的经幢一同衬托出屋顶极强的集聚感,强调了向心思想,有“四方归一”的宗教寓意。此外,五大寺附属建筑中的僧居建筑多以喇嘛小院形式存在,建筑布局与纳西传统民居“三坊一照壁”形式基本一致,单体建筑有具纳西特色的厦子(前廊)、传统的照壁,与园林布置精美的天井一同构成宜人的居住环境。 2.细部装饰 细部装饰方面,雀替、斗拱、梁架、门窗等做法既吸收了明清中原建筑制式和手法,也受到藏式建筑的影响,有借鉴也有取舍。如,汉式雀替的轮廓变化受到藏族柱式中托木的影响;汉式门窗区别于藏式建筑中常见的特色梯形刷色套窗、多层方橼出挑的窗檐;建筑雕饰、彩画、壁画又同时融合纳、藏、汉和多元宗教文化元素。普济寺是个典型案例,其殿门融合了纳、藏、汉建筑风格;正殿前廊汉白玉栏杆雕饰又采用了纳西族常见的“鱼跃龙门”“麒麟望月”等图案;而前廊外侧的六扇木格漏屏上的彩绘图案则同时绘有道教常见的八仙图和藏传佛教常见的八宝图。 除以上常见细部装饰上的差别外,五大寺建筑最典型的不同点则是结合了藏传佛教中重要的转经文化所做出的细部改造。丽江五寺寺院面积相较藏区寺院面积小,均未设置外转经道,于是常在山门、殿堂回廊、佛殿外围或院落围墙处安置小型玛尼经轮,形成连续的内转经道,方便香客诵经祈福。 (五)园林空间构成 丽江藏传佛寺园林根据其功能和景观特点不同可将其空间分为自然环境空间、宗教活动空间、园林环境空间。自然环境空间为佛寺园林景观的营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山水骨架和景观素材;宗教活动空间提供宗教活动场所,主体建筑群布局对称规整,表现神秘森严的宗教气氛;园林环境空间则提供了休憩娱乐的场所,同时过渡了宗教建筑与自然空间。根据周维权所提出的三种寺观园林环境的形态[18],结合丽江藏传佛寺园林环境特征,可将其佛寺园林空间划分为寺外园林空间、庭院空间、附园空间三种类型(图5)。图5丽江纳西族聚居地藏传佛寺园林空间位置示意图1.寺外园林空间 主要指佛寺入口的引导空间和佛寺周围将自然景观组织转化为可供观赏的园林化空间,丰富了佛寺园林环境。五大佛寺充分利用寺外园林空间布置佛塔、本康、经幡等附属建筑,既可供观赏也满足了宗教需求。 2.庭院空间 由寺院建筑围合而成,穿插于生活及宗教空间。五大佛寺内庭院独具清新淡雅的纳西庭院特色,庭院空间适度,通过布置花台树池,种植花木,烘托宗教气氛,并穿插、点缀各式盆景及景观小品,形成人与环境、世俗生活与宗教朝拜相融合的园林空间。 3.附园空间 位于宗教主建筑群一侧,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园林空间。园林结合地形,营造出层次丰富的景观、美化寺院环境的同时,也为香客及僧侣提供游览观赏的活动空间,还兼有种植生产的功能。 五大藏传佛寺园林在保持宗教空间主建筑组群规则式合院布局前提下,随地形的起伏或转折灵活布置园林空间,三种不同类型的园林空间形态将佛寺内外空间组织在一起,达到宗教精神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融。 (六)空间组织 空间序列组织的好坏关系到园林的整体结构和布局的全局性,按一定秩序组织的园林景观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带给朝拜者思维空间的变化[19]。 五座寺院均设有前导部分,由前导香道和寺前广场组成。寺院选址均位于山间,通过在入山香道两侧布置宗教小品(如经幡、佛塔)或是搭建构筑物(如商业走廊)引导视线和行动方向,酝酿香客的宗教情绪和游赏兴趣,也是世俗社会向宗教社会过渡的象征。寺前广场连接香道与宗教建筑空间,既为宗教法师活动(如跳神活动)和来往香客游人提供集散场所,也是寺内外园林空间的过渡。 空间处理中,常通过对宗教建筑空间进行对比、渗透等处理以达成空间的多样统一。以普济寺为例:寺院面积较小,受地势影响不能通过纵向轴线营造多层次院落空间,则利用空间处理手法使园林空间极富趣味性(图6)。普济寺共设置两条游览路线,主游线方便香客进香朝拜,沿中轴线可快速到达主殿;次游线运用空间转折、渗透、对比等处理手法,延长游览时间,营造丰富的景观。主游线由点A(山门)进入,经由前院和前殿,至点B(后院),重复两次空间“收—放”,形成对比与变化,打破小院落空间的局促,同时又凸显出主殿的高大;次游线则通过设置C、D两处狭长过道以进行空间收束、引导,暗示香客前往南侧两僧院及附园,同时设置月门连接对景观进行渗透与过渡。图6普济寺空间结构分析图 (七)植物配置 纳西先民创造的署神是世界上第一个司掌自然万物的生态神,被认为是人类同父异母的兄弟,后代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保护森林等自然环境的生态观[20]。纳西人素来爱护且崇拜植物,喜爱在庭院内养花植草。加之明清时期汉文化在纳西民间的广泛传播,佛寺成为文人雅士研习文化和交往聚会的场所,因此,丽江五大藏传佛寺园林植物配置较其他地区更加丰富且独具地域个性。 1.乔木 古树是寺庙园林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见证,五大佛寺古树在丽江古树中占有量较大。根据对现存古树进行调查统计得知,出现频率较高的乔木依次为干香柏、圆柏、雪松、铁杉等为主的松柏杉类树种以及山玉兰、梅、红花高盆樱花、丹桂、云南含笑、银杏、国槐、大叶紫薇、云南山茶、桃、梨和黄背栎、昆明朴、高山栲、滇石栎等特色树种。五寺中除运用了较多佛教寺院中常见的梅、丹桂、云南山茶等具有生态、经济以及观赏功能的常见树种及乡土树种外,还栽植了被赋予纳西民族文化内涵的“神树”[21]。其中,松柏杉类树种所占比重最大,除其极具耐寒瘠的特性适种于山地环境,能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外,也与其具有的“常青”象征意义有关,而在纳西东巴文化中,柏树与黄背栎分别被认为是“天母天舅”“天父”的代表,也是祭天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元素[22]。五寺中必栽植的山玉兰在纳西东巴文化中则被称为神树,称“含依巴达”,是生命的象征,被奉为万木之尊,因此无论是纳西民居庭院还是寺院、学校等地都多有种植[22]。 2.灌木与草花 丽域五大藏寺僧侣结构多为纳西族人,自古喜“植树养花”。不难发现,五大寺内庭院精致小巧的园林布置与古城民居庭院极为相似。寺内于附园及庭园空间布置大量树池花坛及花盆栽植灌木与草花,树种则多选择黄杨、女贞、山茶、云南含笑、杜鹃、绣球、月季,与纳西民居院落中常用的草本兰、菊、大丽花、灯笼花等共同构成乔木下层空间。外形修剪整齐的黄杨、女贞与山茶、含笑等观花植物一同从视觉与嗅觉上衬托宗教氛围,而兰、菊等草花遍植花坛与盆景内,起点缀与过渡作用。 (八)铺地 丽江藏传佛寺园林中将纳西民居庭院常用的生态铺地运用其中是较为特别的,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纳西生态铺地常采用卵石结合砖、条石等材料组成拼花地面,常见拼花图案形式包括动植物、宗教图案、几何图案及文字式样,一般多是一种或几种图案形式组合[23]。常见的四福拜寿、“蝙蝠”“祥鱼”等装饰图案与宗教题材相结合来暗喻追求现世的安康富足、长寿繁衍,体现纳西族文化中的生命崇拜;指云寺外广场更是在铺地中运用了纳西族十二生肖图案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图7)。此类铺地不仅利于渗水,具有生态功能,同时利于铺地图案的色彩、材料、大小、质地等多种对比和变化,能够形成丰富的色彩效果和花纹图案,丰富园林空间,也体现出丽江藏传佛寺园林的独特之处。图7佛寺卵石铺地拼花类型图四、结语 五大藏传佛寺的建立得到了土司和官府的支持,在选址上占据了良好的地理位置;建筑群布局则根据山势结合平面与竖向上的空间变化,突出正殿的中心位置;而在建筑形制上,则是融合了纳、藏、汉三种风格,细部装饰添加了道教、东巴教等多种元素,满足信众需求;作为历史上文化名人交流聚会的场所,五寺对园林环境的营造及植物配置等方面十分用心,布置精美的院落空间则与纳西民居庭院类似,极具生活化气息。 多元文化交汇背景下,纳西人对宗教信仰“信而不笃”,面对多种宗教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勇于创新”的同时,也始终保持其纳西文化的主体地位。纳藏悠久的历史渊源为藏传佛教在纳西族聚居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五大藏传佛寺“教不参政”“寺院间无隶属关系”等特点使其只能结合地域文化传统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当地社会发展,这直接导致其宗教趋于“世俗化”“生活化”,也使其园林环境具有了典型的地域特征。 ◆◆◆◆◆◆◆文中所有图表均为作者自制、自绘。[1]丽江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年丽江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zz/8000.html
- 上一篇文章: 五月盆花市场谁在唱着ldquo欢乐颂
- 下一篇文章: 西河大鼓兰桥会爱情无不因凄美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