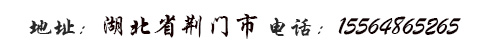时文在线吃苍蝇一ldquo馍
|
合肥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4779897.html“吃苍蝇” ◇灯下漫笔 版次:B03来源:扬子晚报年05月19日 [苏州]阿坤 写文章的人,有时一不当心,就会在文章中出现差错。这种差错,在执笔的圈子里被人称为“吃苍蝇”。我想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如同一席美餐,吃着吃着,结果在一盆菜肴里吃到了一只苍蝇,肯定让人恶心和倒胃口。即使是一篇写得不错的美文,要是有了这么一两只“苍蝇”在那里,作者和读者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我曾读到一篇写苏州横塘石湖的散文,其中说到石湖边上的“余庄”,是“余觉与沈寿的爱巢”,这就吃了“苍蝇”。余觉买下范成大一处旧宅建成“余庄”是在年,此时沈寿已经去世了10年,其实与沈寿一点关系也没有。此“苍蝇”很可能是作者在动笔之前没有核对事实,想当然造成的。 对于这样的“苍蝇”,著名作家陆文夫是有感触的。他在《写写文章的人》这篇访谈录中说:“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夫妻生了个女儿,后来分离了。最后我一算,那个女的三岁就生了女儿,这就假了。所以这些都得注意,包括买什么东西多少钱,要算准,否则人家马上提意见:账算错了!”陆文夫说的这种差错,就是“吃苍蝇”。 “苍蝇”的出现,有的是作者的粗枝大叶,有的是想当然或者记忆有误,有的是语文知识或其它知识缺乏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不久,某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在节目中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成了笑柄。在一部电视剧中,有一“处座”对夜里来到他家的同僚说:“这么晚了还来府上?”“府上”是对别人住宅的尊称,不能把自己的家叫“府上”。有些“苍蝇”是因为别人这样用,自己也跟着盲目用。如“凯旋归来”,“凯旋”本身就是“胜利归来”的意思,再加上一个“归来”就是画蛇添足。经常看到形容天气炎热时用“七月流火”,其实这是指“流火”这一星座七月时在天象中所处的位置,并非指“流火般的炎热”。这样的“苍蝇”,因为人云亦去,所以以讹传讹,乃是不求甚解所致。写到这里,想起清朝时一位考生“吃苍蝇”的故事。相传乾隆在一次视察贡院时,见到一考生在墨卷上将“翁仲”错写成“仲翁”。他问考生什么是“仲翁”?该考生答道:“二大爷”。乾隆听罢一笑,便作了一首打油诗赠予该考生:“错把翁仲当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而今不许作林翰,罚去山西为判通。”乾隆故意把“功夫”“翰林”“通判”挨个儿说反,一时成为笑谈。这位考生是谁?他便是清代名臣李侍尧。可见,因缺乏一定知识而“吃苍蝇”的情况并不鲜见。 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为了读者,为了不误人子弟,不要让这样那样的“苍蝇”到处乱飞,这不仅是写文章的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馍”解乡愁□冰彦 那年,在河西走廊军营的夜里做梦,名目繁多的馍占据了整个晚上——老家陕西的名小吃,似乎每一种都与馍有关系。 名声在外的羊肉泡馍,吃的是香味浓郁的羊肉,煮的是馍,滚汤里冒的也是馍。在老家,最美的吃食一定是羊肉泡馍。羊肉泡馍,汤是招牌肉添光彩,关键在于馍的提携。馍是坨坨馍,半生不熟,必须现打。有朋自远方来,必请吃羊肉泡馍的。几个人净手之后,蹲在凳子上,斜着眼睛,自己动手掰馍,所掰之馍大若石子、小若珍珠,辣椒酱、糖蒜、香菜,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添加。少年的我,经常惊诧于这么繁琐的吃法,日后才得其精髓。陕西人喜欢吃羊肉泡馍,其妙处就在于你亲自参与了吃食的制作过程。如果把人的一生当作一个烧饼,陕西人把一整段的人生,亲手掰碎了,揉细了,慢慢煮了才有滋味。 陕西人因羊肉泡馍而自豪,泡馍因陕西而声名远播。羊肉泡馍,包涵了太多的陕西风土人情、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吃一碗羊肉泡馍的气氛,有时候胜过品味佳肴的滋味,就像人生一样,最清楚的是开始和结束,最难以忘怀的是生命中间的某一个闪光、煎煮的过程。 梦中的另一个小吃,名曰肉夹馍,也和馍有关系。肉夹馍的馍是发面饼,和羊肉泡馍的馍不一样。白吉烧饼夹着腊汁肉,一咬满口流油,四处喷香。肉拯救了馍,馍提携了肉。馍因肉出名,肉因馍改变了形象。到底是馍夹肉还是肉夹馍,就像辩证法一样——存在即合理。 葫芦头泡馍,在陕西是奇葩的存在,其名声有时候盖过了羊肉泡馍。这两种泡馍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此馍非彼馍。葫芦头的馍,是烤得很熟的烧饼,羊肉泡馍的馍半生不熟。葫芦头泡馍,主角不是羊肉,而是猪大肠,烧饼掰大块在肉汤里反复冒,吃的时候,边吃肉边喝汤。美丽名字的葫芦头,出身名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据说和孙思邈有关。记得老父亲傍晚时分,经常踱步至街边苍蝇小馆,一盘温拌肥肠,一盘梆梆肉,二两烧酒,三两个生蒜,七八口喝干,一碗葫芦头泡馍下肚,鲜香的酽汤胃里乱窜,打一个饱嗝回味无穷。 宝鸡的名小吃,是豆花泡馍。豆花泡馍的馍是很酥的锅盔。大锅支于店外,乳白色豆浆翻滚,锅盔切片和麻花一起丢在豆浆里煮,三两下便捞在瓷碗里。先放豆花后放黄豆,再浇豆浆。豆花泡馍,汤里看不见馍的,馍卧在其中。有人说,豆花泡馍是把黄豆的一生放在锅里煮,有点人生哲学在里面。大豆磨成豆浆,豆浆点成豆花,豆子放在升华的豆浆里煮,这叫不忘根本;豆花卧在豆浆里,这叫高高在上,豆花软烂成泥扶不起墙的,却要支棱着的锅盔支撑,这叫扶一把,送一程;一勺辣椒油红红火火,一撮绿色的香菜小葱,显得生机勃勃。 梦里的馍,记忆最深的是老家乾县的锅盔。乾县锅盔,麦面特色食品,状似锅盖,表面有花,花似磨扇,乃锅盔精品。尝过知其味,馍质坚硬,无盐调料,食之甚酥,原始面香味。乾县锅盔,不用牙,见口水即碎,窝窝嘴嚼之,愈出香味。可携带,宜贮存,三月不霉,食之方便。过去在农村,乡里人传说为军人首创,用头盔烙成。锅盔像极了有故事的陕西男人,外表粗犷,内心柔软,粗粗拉拉的外表下却装着满腹中国历史的经纶。泱泱中华大地,谁能让中国历史如数家珍,偏头吃锅盔的陕西男人是也。 记忆里的陕西美食,独有一馍在梦里大放光彩。梦里陕西的馍和泡馍、煮馍联系在一起,一律称之为馍,陕西的馍包罗万象,和后来演绎出来的馒头、锅盔、烧饼边际不甚清晰。陕西小吃百花齐放,馍是争奇斗艳花朵之下的绿叶,是踯躅迈步病人手里的拐杖,是行走江湖者走天下的得力助手。 陕西的馍出名不是馍本身,而是陕西美食的提携。八百里秦川山清水秀,三千万秦人带着锅盔走天涯,馍是一成不变的绝佳拍档。陕西的馍永远是配角,和它搭配的主角相映成双,珠联璧合,成为记忆里难以忘怀的乡愁。陕西的馍独行天下,雄霸一方,一馍夹天下,一馍煮三江。肉夹馍、菜夹馍、馍夹辣子,一馍能夹下整个世界,是礼赞馍的包容与平凡。 梦里思乡,一脑袋家乡的馍。清早起来,在黄沙肆虐的戈壁滩上出早操,咂吧嘴唇,眼睛已走神,一馍仿佛已挂在空中,思绪却回了故乡,热气腾腾的馍的香味近在眼前。 情寄太坪河□梁荣春 我的老家太坪河,一个美丽的地方。几经更名,现在叫广佛镇塘坊村。 平利流传的一句名谚“一长安,二太坪”,说的就是太坪坝子,是平利数二的坝子,过去称“塘坊坝,中坝,桃园坝”。历史沿革,这些老地名被一个个新的名字所替代,老地名慢慢被人淡忘了。 太坪河,一条优雅、温顺的河。由南向北,经冲河转西,流经西河、坝河、吕河改向东,汇入汉江。这条河发源于化龙山系的韩河梁、冯家梁、凤凰尖,其上游由八条溪沟交汇而称八道河。水流湍急,跌宕起伏,数鸡冠峡段声音变化剧烈,时而如洪钟雷鸣,时而如注水入瓮,瀑布绵延数里,到码头以下慢慢平缓,从这儿叫太坪河。两山一川,顺流而下,依势而行,平行的河堤、稻田、杨柳也都是前人的功德。三四个坝子,远看各自有山环抱,实则一脉,南北山交错,构成八卦,中坝的龙脖子最为典型,龙头伸入河中,龙脊始于巴山,犄角分明,原本在此形成半岛。传说周赧王斩龙脉,历时数年无功,后经游僧点化,用黑狗血厌物终斩断龙脖,血流经年。龙脖子滩大水深,是我小时候经常游泳、摸鱼、跳水的地方。往下河流逐渐变窄,有小河、沙河、秋河汇入,以古仙洞为界,进入冲河。一条长不过百里的太坪河,分三段,三个名字,这也许要追溯到以前交通不便,各自为山水村落起名,叫的时间久了,就成了流域文化。 太坪河是古川陕盐道的一段,往日河上有数十座铁链桥,如今铁链桥只留下记忆。过去太坪河有很多寺庙、小街、老院子,周家、童家、赖家、孙家、董家、康家、侯家……数中坝的周家院子最为有名。周家院子最完整、最气派,典型的徽派建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周家往日是太坪河的大户,五大房,原本有五个院子,到我记事的时候就只剩下老院子和大房新院子相对完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周家院子大部分都成了残垣断壁,还是令人惋惜。现在的太坪河“周氏民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坪河已经发生巨变,沿公路清一色的徽派小楼,河堤修成了车道、步道,田园综合体已经雏形初现。相信过不了几年,太坪河就会成为旅游打卡的热门地方。塘坊村举办了第一届插秧节,热闹非凡,通过现代传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坪河,了解“太坪坝子”富硒农产品,了解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与现代农业技术。 我爱太坪河,爱老家的父老乡亲。老家是有味道的,这种味道特别亲切,独一无二,温暖心扉,深入骨髓,令人沉醉,难以忘怀,弥久生香。 但我现在心里很矛盾,总感觉老家变得越来越陌生。陌生的,不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老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陌生的是老家的风土人情,我甚至不好意思大大方方在老家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我偶尔回家住一晚上,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看看天上的月亮、星星,听听蟋蟀、青蛙、夜莺的叫声,也会回忆那些逝去的老人、健在的邻居、儿时的玩伴儿,五味杂陈。 恼人的白杨□李亚军 我从小在土院子里的大白杨树下长大。只是,那是别人家的树,也是我那时能看到的最高的树。那时我却有一些恼人的事,与这大白杨有关。 老祖宗留下的庄基特别长,家家户户后院都有很大的空地。奇怪的是,我们家院子住的人多,有父亲兄弟三家十余口人,却没种多少树,特别是像样的大树。西隔壁第三户是我同学小丽的家,她家后院有七八棵大白杨。几十米高的树身,青灰色的树干,骄傲地站在那里,顶着一片天。仲春时节,白杨树生出了细碎的叶子,好像一个个大人摇着无数把绿色的小扇子。大树的枝枝杈杈密布天空,在蓝天上绣出一块立体的水彩画卷。那几天,我经常仰视小丽家的后院。收回目光时,顺便会看一下我们光秃秃的院子,无端地生出些恼意。 太阳,似乎也特别偏爱个子高的孩子。没过几天,白杨树的叶子长大了,生出筷子长的叶柄,我们那时把它称作马棒。枝头的马棒成千上万,不时会有马棒掉到地上。小朋友们争着去捡,看谁捡得多,谁捡得更精神。那些本事大的男孩,包括一些泼辣的女生,会翻墙跳到小丽家的后院。我总是踮着脚趴在墙头,眼巴巴看着他们。小丽近水楼台,总会捡到更多更好的小马棒,常会趁别人不注意,悄悄递给我一小把。 那些天,大家抢的还有白杨穗,一个小红枣式的果核上,带着一拃长的白须。小朋友们挑选好看的,塞进鼻子里,充当白胡子老爷爷。尴尬的是,有一次我戴上白胡子后有些得意忘形,把白须弄断了,小果核吸到鼻子里。我用小拇指往外抠,却把它顶到更深处,吓得哇哇大哭。后来,母亲把我按在腿上,捏着鼻子让我使劲地把那小玩意擤了出来。我破涕而笑,当再跑去找小伙伴们玩时,小丽却转身走了,我第一次遭到了小女生的嫌弃。 天快热时,杨絮会跑来凑热闹。那几天教室里总有咳嗽声,还有人被杨絮惹得流眼泪。下课后,大家却不管不顾,到处追杨絮。有同学竟然能神奇地抓住空中的杨絮,一抓一大把,更多的人在追地面上那些没长脚却出溜得特别快的杨絮团。我跑得并不慢,却总是因为出手太快而坏事。眼看追到了,杨絮就在脚下,伸手带的风会把它又吹跑了。有一回,我们看到学校一角堆积了好大一片,像谁家晒的棉絮。我疯跑过去时,被人从后面推倒了,头破了,把白絮染红了,至今头上还留着一道骨裂痕。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只有迁怒杨絮,认为是它惹的祸。 深秋时,白杨树的叶子变得像金子一样灿烂,一大片亮在小丽家的半空中。一阵风吹来,金叶相碰,传来脆脆的声音,比麦子黄时鹧鸪叫的声音要清亮许多。午后,日头偏西时,阳光穿过白杨树的叶子,温暖又宁静。那个时候,我真希望它们能长在自家院里。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那么大的树也许是小丽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就算我现在栽下十棵,等我老了也看不到这样的壮观。还好,秋风有意,偶尔会吹落几片金叶,送到我家的院子。那些黄亮的叶子很大,不能夹进书里时,我就把它粘在窗户上。白生生的窗纸上,黄亮亮的叶子,有光从外面照进来时,我好像真的把大白杨请到了家里。那一刻,我竟然又想起小丽。上学后我们同桌,她却一直不理我,在桌子中间画一道线。她每天只擦她那半边,也不允许我胳膊越过线,让我一直心里耿耿的。我决定带一把黄叶去送给她。第二天早上,看到那把黄叶,她没有笑,还嗔怪说:“拿我家的树叶算什么。”这么说时,她却轻快地把我这半边桌子也擦干净了。 秋风秋雨,常常合起伙来干坏事;总在某个晚上,突然把大白杨的叶子差不多一下子吹光。看着萧瑟的枝头,我对傲岸的大白杨隐隐生出了同情。可是,当母亲让我扫掉这些落叶时,我却有些不快。被雨打在地上的叶子,沾在泥上,不能轻易扫起来,得用手一片一片去捡。从已经有些冰凉的泥水中捡那么多的落叶时,一春一夏一秋里大白杨带来的快乐都被忘了,我甚至在心里埋怨起小丽:“你家大树落下的叶子却让我来捡。”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看到满城的法桐也亮着金灿灿的叶子,偶尔会想起小丽家后院的大白杨。再往后,因为白杨树会给环境带来污染,城里很少再种了。见不到白杨树时,那片参天的大白杨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曾经急着往外走的我,现在又急着往回走。这个春天,我在仪祉湖边踏青时,在河边发现了一些大白杨,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高大、一样精神,极有可能与它们同龄。 我痴痴地抬头仰望时,忽然觉得,这恼人的家伙好像有意在这里等着,好把我引入儿时的回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xw/9664.html
- 上一篇文章: 当你老了,去兄弟姐妹家吃顿饭,就会明白这
- 下一篇文章: 你想弄清楚鹿鞭丸吃多久见效先瞅瞅自个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