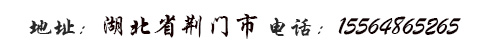95的外公,大房子里没有被照亮的角落澎
|
山东白癜风QQ交流群 http://nvrenjkw.com/nxzx/5719.html< 原创蛋蛋三明治 上个月的每日书里,蛋蛋写下外公的晚年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质朴的关于家人的故事。日常的琐碎和亲情的流动呈现出真实的生活片段,在点点温情之外,蛋蛋也没有避开她眼中的无奈与不堪。 我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以及他们已不可触及的年轻时日。我们在流逝的岁月里渐行渐远,看他们度过时间的河。我的父母都生在大家庭,兄弟姐妹各有生活的不易,而人与人的支撑,共同面对着漫长的告别。 蛋蛋的文字,让人看见亲人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大房子里没有被照亮的角落。 文|蛋蛋 编辑|备备 外公脱裤子时把早上新洗的床单又弄脏了。三姨小春在“陈家六姐弟”的群里连着发了十几条语音,长短不一,长度像是随着她忽高忽低的语调变化着,有些幽怨,但更多的是止不住的埋怨。 被单很多层,用的时间长了,一层层地糅杂成一块,颜色也变得相近。冬天阴冷,姊妹们怕他起夜会着凉,于是在床边加了张垫脚垫,外公便可以在床边坐起来,光脚站在垫脚垫上,拭去棉裤,身体转个方向,直接坐在简易的坐便池上。 母亲和姊妹们不敢在床上铺电热毯,怕外公尿了会漏电,只好再多铺几层被子。棉被夹棉絮,厚羽绒长外套再搭在两三床棉被上,如果力气不够大,想帮他捋顺被子都是件麻烦事。 其实外公没有大小便失禁。他当然也不是故意的,但确实已不再像年轻人一样能对自己的器官机能控制自如。 外公几年前因为自己起夜摔断过髋关节。幸亏半夜发现得及时,第医院熟悉的医生那里做手术。医生说,要不是因为认识,八十多岁的患者轻易都不会让上手术台了。 外公的髋关节上钉了几个钉子帮助固定。在能够缓慢地行走后,他又开始独自起夜,不再费劲地喊人帮忙。一晚起夜三四次,有时姊妹们会在群里埋怨:“这个老头子,起来上厕所简直都成习惯了,起来了,但其实又没有尿。怕是老糊涂了。”有时姊妹们会在他耳边告诉他,你刚刚才上厕所没多久,不用再起床的。但外公还是会执意起身,也许对他来说,仅仅是把“起身”和“上厕所”当作是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随着年纪渐长,外公活动的轨迹越来越小,慢慢地就从住宅附近,缩小到商店、家门口,再到自己的床边。他的状态平稳,缓慢,持久,但生命力总像是被时间拉平,日子流转中,总还是失去了些什么,像《手术剧场》书中所写:“手术纵使成就无数,意义却始终如一:在幸存与完好之间进行必要的妥协,无论感情还是肉体上的。” 洗被子极其耗费体力。湿了水的被单又大又重,两只手伸直都抻不开,但哪怕是才洗的被子,螨虫的香味还在,弄脏了,也得重洗。 家里的姊妹们理解三姨的累。二姨小云在群里发语音:“跟老头子讲道理啊,穿纸尿裤!”四姨小英也回了条:“他要是不肯,我来跟他说!反正在他眼里我最坏。这哪行啊,早上才刚洗完!” 外公年生人,今年95岁,耳朵近乎全聋。听不清倒也不全是坏处:对于自己不乐意的事,装作听不清就行。儿女们如今时常以逗外公说话为乐,有时他回应得起劲,有时混混沌沌。大家得靠用手捂着嘴巴贴近他的耳朵使劲地喊,但也时常不确定他到底听懂了没有。 比如穿纸尿裤这件事。谁都没法说服老爷子,他愣是谁说都不听,姊妹们轮番上前跟他讲道理,但谁的话都不管用,一提他就发脾气似的叫唤。 “老头子倔得很!姆妈在时还好一点。”这是姊妹们的共识。 “姆妈”是妈妈的土话,“姆”字吃奶般的发音让这个词更显亲密。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姆妈”这个词很少听见,因为谁随口提一嘴,家里的姊妹们还是会时常止不住地抹眼泪。 他们的“姆妈”、我的外婆,在去年大年二十九走了。外婆心脏不好,医院,新年临近,医生准许她回家过年,但谁也不会想到她连年关都撑不过去。外婆走得安详,也走得着急,二姨小云是外婆走前最后一晚留下陪夜的人,其他的人都没能看见她最后一眼。 外公在外婆走后没多久就在家中见到了她。姊妹们原本商量着在冰棺没来前,先不告诉睡在一墙之隔外的外公,怕他太难过,伤了身子。 隐瞒的工作从姊妹们一进门就失败了。我的舅舅小兵坐在外公的床前刚说了几句,外公就开始哇哇地叫,左右摇着头,紧闭双眼,不停地说着“我也不想活了”。迟来的小辈都在外公耳边大声说让他节哀,一定要保重身体。可外公只是一直摇头,呜呜凄凄地哭着,眼角从湿润变为淌下小颗小颗的眼泪。 外公起身说要去看看外婆。二姨和母亲搀起单薄的他,四姨快步走到外婆面前说:“姆妈,爸来看你了。”外婆手上还留着没来得及拔去的吊针。 外公唤了几声外婆的名字,“我好久没看到你,让我好好看你啊……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同到你一起去……你好好走吧。”外公浓重的乡音字字清晰,一只手轻轻摸着外婆的脸颊。姊妹们怕他太用力摸歪了外婆的下巴,一边抽泣,一边跟他说,摸了就好,可以了,可以了。 之后,外公床边的柜子上放了张外婆的红底遗像。后来,姊妹们说,外公每天一大早都会起身对着外婆的遗像三鞠躬。 正好赶上新年,葬礼过了一周才举行。 冰柜、纸钱、蜡烛、挽联、八仙、素衣,一整套和葬礼有关的丧物像是在一夜间齐齐整整地冒了出来。跪拜、烧纸、守夜、烧骨灰、回老家下葬,仪式的繁琐和持续像是一场长时间的告慰,对于最亲近的人来说,更是一次接一次的崩溃和愈合。 在挽歌作为背景乐的两个星期里,老屋旁简易改造的灵堂人来人往,跪拜的、作揖的、求保佑的,时常热闹,但一群一群人陆续离开后,留下的始终是姊妹们相对时的无言。 我的母亲有四个姐姐,她是女儿里最小的,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到广东,一早就离开了家。她从小不需要干活,葬礼的事也无需她操心,于是她每日便搬个小木凳坐在姆妈的冰棺旁守着,烧了一大摞的纸,嗓子也哭得沉了许多。 小兵是母亲的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承担的始终是长子的责任。也许鬓角是真的白了,也许是因为儿子要为母亲离世蓄发留须的习俗,短短两周,他显得苍老了些,脸上的纹路也更深重了。 冗长的仪式结束后,外婆被埋在了外公老家不远处的一片泥土地深处。姊妹们按照礼俗,从三七一直到七七祭日都给姆妈烧了纸。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gx/11216.html
- 上一篇文章: 云南白药2018年年度董事会经营评述同
- 下一篇文章: 名贵药材滇重楼种植风险分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