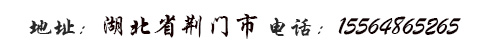我已为你叛国,离家,失亲,现在能亲你一下
|
作者 橘文冷画师 鸦青染歌曲 玄觞 5时光荏苒,转眼金风乍起,玉露渐生。这夜,定国将军府。亥时三刻了,一个多月以来,每晚的这个时候下人就会将煎好的药送来,今夜稍稍晚了些,但卓长恪也不是那么在意。揭开瓷盖,浓浓气味便散发出来,混合着甘甜和苦涩的药香。这药不好喝,但是十分有效。那个叫夏浅雪的丫头,杀了其实有些可惜。他一边喝着药一边这样想,或许想个办法将她逐出宫去……说起来,那个什么淳儿该如何是好?不知不觉一盅药都饮了下去,效果立竿见影,头痛缓解了许多。将药盅搁到一边,下人自去收了,“将军早些歇息。”道过这一声,人就退了出去,并顺手合上了房门。他吹灯上榻,躺下时还在想着日间与几名心腹商议的大事——边境的探子来报,大夏最近似乎又有动静了。他想调兵到边界水阳江那里,先占地利,凭水阳江天堑,未必不能与大夏一争……想着想着,意识便渐渐模糊了……忽然他浑身一激灵,猛地清醒过来——军旅生涯多年,他作为一个武者的警醒是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的。屋中有人。那人点亮了烛火。他睁开了眼睛,诧异地看向来人:“是你?”只说了这两个字,他就觉出自己的声音异常嘶哑,嗓眼还伴着火燎般的疼痛。不由得暗暗心惊。眼前的来人是夏浅雪,她还穿着那身太后所赐绣着折鹤兰的绿衣,神色很平静。他想起身,却发现自己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也没了,他毕生从未真正恐惧过什么,但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控的情况。“奉太后令,来看看将军服药的效用,顺便……”只见夏浅雪在榻边坐下,低声说着:“送将军最后一程。”身体益发的沉重了,之前因为惊醒而生的一点清明也在消散,他想到自己或许是中了毒……但是眼前的女子只是开了方子而已,药都是自己的亲信所煎。但是看她能在府中来去自如……“君、君上知道……必、必不、饶……饶……”他的舌头也开始僵硬了。“将军勿忧,此毒毫无痕迹,不会有人怀疑到浅雪的身上。”那低沉悦耳的声音,渐渐变得遥远。他放弃了再说更多的话,只是想到了那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鹤兰,你当真如此不能容我?鹤兰……他曾经爱过的人,后来又失去的人。亦是与他纠缠至今,爱恨难解的人……眼前,只剩了绿衣的模糊身影。忽然间这身影又清晰起来,李阁老的家中,穿着自己所赠新衣的少女晕生双颊,说:“你怎知道我最喜欢绿色?”“鹤兰,你穿这衣裳,真好看……”“拿刺客!”子夜时分,当将军府的家人发现卓长恪房中有异常的说话声,叫来卫士冲进房内时,看到的是满面惊诧之色的夏浅雪,以及——榻上已经没了呼吸的定国将军。“这怎么可能?!”卓无涯被内侍以国君口谕紧急传召入宫,内侍只说出了大事,待他看到眼下青黑的文重君,听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不由得如此惊叫出声。夏浅雪杀了卓长恪?怎会有这样的事?若说卓长恪今日杀了夏浅雪……倒还有些可能。最初的震惊过后,他开始分析方才兄长所说的细节:“既然查不出定国将军的死因,如何能说是夏姑娘所杀?”看文重君若有所思,他也随之考虑种种可能,忽然心中一动,身子不由得一僵。“可也不能因此就说定国将军的死与她毫无关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安若太后的声音。“本君已吩咐过他们不要惊动母后……”文重君有些恼怒。他退开几步,看着母亲走到兄长身边。“定国将军是我云罗重臣,如今死得不明不白,哀家又怎能置身事外。”安若太后神色凝重,接上了方才的话题:“哀家听说,那夏浅雪三缄其口?如此必是有隐情……君上……”她走到文重君身边,“须知如今之势,她身在现场,必然脱不了干系,君上也须给文武百官一个交待。”她的声音压得如此之低,但他在一旁还是听见了,只觉一股寒意涌上了背脊。但见文重君神色犹豫,“且容本君想一想。”“请君上明断。”安若太后点了点头,往一边去坐了,似乎是一定要等到一个结果才会罢休。而直到文重君做出决定为止,他都没有再说哪怕一句话。关押夏浅雪的地方并非刑部的天牢,而是梦昙宫深处的黑狱,深在地下,不见天日,负责看守的狱卒都是不识字的哑巴,以确保这里发生的任何事都不会传扬出去。听到一前一后两个脚步声时,夏浅雪睁开了眼睛。狱卒将来人带到后便退走了,她看着来人,轻叹:“久闻梦昙宫下的黑狱森严谨密,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太后真是高看浅雪了。”安若太后在离牢门一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姑娘是九王爷的人,哀家岂敢托大。”“原来太后还记得与九王爷的约定……那岂不知我死,九王爷不会善罢甘休。”她抬头仰视。“九王爷只会得知你出了纰漏被擒,定罪受诛,又与哀家何干?”太后的神色忽然冷峻起来:“杀了卓长恪就够了,哀家不会放任你继续行事……”果然是猜到了呢……她心中不由得苦笑。可是……其实她本打算过了今夜,就永远离开云罗的。“太后就不怕我说出实情么?”“你不会……若说出实情,淳儿必然受累,”安若太后很是笃定:“眼下,沉默是你最好的选择。”她无言以对。忽然眼前黑影一晃——“什么人?!”安若太后猛地回过头去查看,但她什么也没看到——因为那黑衣人已转到她身后。她看着那人打晕了安若太后之后就上前来开牢门,只见他在一大串钥匙中寻找合适的那一把,急得两手都在颤抖。“令君?”她试着喊了一声。黑衣人全身一震,伸手拉下了蒙面的黑布。正是卓无涯,他的脸色那么苍白,火把的光映在他脸上,照见挣扎的神色。可牢门打开后,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一把拉上她就向外跑。一路上,只见倒地的狱卒。她的心一点一点凉下去——竟为了她做下这样大不韪的事,该如何是好?卓无涯轻功卓绝,对梦昙宫又极为熟悉,出了黑狱后他带着她自宫中的隐秘小路走,在一处偏僻的夹道中有一扇失修的门,外面是准备好的马匹。她上了马,却不想他也随之抓着缰绳想跳上来,她按住了他的手,摇头:“现在回去,太后不会说什么,令君明日依然是令君。”只要他回头,安若太后会护着他,文重君也不会自折手足,他依然是云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靖疆令。不要为了她,失去那么多,她自问偿还不起。可是……只见他仰头笑了笑——随后,翻身上马。选了亡命天涯的路。“浅雪,可知在第一次见你时,我就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的,总有一天我会为了你做大逆不道的事,并且……甘之如饴。”马蹄声疾,她骑在颠簸的马背上,听耳边卓无涯温柔无奈的话语,感觉着身后他略见急促的心跳,不由得陷入沉思。6一夜奔袭,天将亮时他们到了一处湖边。水草丰美,卓无涯一勒缰绳,先行翻身下马,随后又抱她下来。“这是哪里?”她问。“狭玉湖……已离锦华城两百余里,很安全。”他抚着马儿黑亮的长鬃说道。她听了,默然片刻——“那么……我与令君,就在此地别过。”却见他一笑,“浅雪,你是替母后做事的,对不对?”她眨了眨眼,而他接着道:“或许君上觉得应该装糊涂,永远都不会去说破。但我知道……想要叔父死的人,只有母后。”他看着她,神情忽然变得有些悲伤:“其实你不是医者,而是鸩者。”这不是疑问,是在陈述事实。而她,无从反驳。鸩者,饲鸩鸟,制奇毒。传说中,只要用鸩鸟的羽毛浸入酒液便成剧毒,但事实上毒药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于是就有了专擅此道的人称为鸩者。而因为医毒同源,鸩者也需通医理,越是优秀的鸩者医道也就越是高明。“还记得你我初见么?你袖箭上的毒见血封喉,是我生平仅见……”卓无涯说得有些艰难,似乎是不想将这恐怖的剧毒与她联系在一起,“还有叔父那些新生的黑发,我曾听说那是黑鸩之毒在体内聚集的症状,以此毒可杀人于无形,死者外表看来一无异状……”“令君既知我是怎样的人,又为何要救我?”她打断了他的话,也等于承认了他的话。“对于母后来说如今你已是弃子……”他说起事发那夜的情形——宫中赏桂,安若太后说可惜定国将军未来,并向文重君提议或可赐桂花一枝。因为如此,文重君才会于深夜派人到定国将军府,府中下人才会前去定国将军的寝室查看。“太后的心计,浅雪甘拜下风。”她听了这样说。却见卓无涯望着自己:“但对我来说你不会是弃子,永远不会。”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是为了扰乱她的心思么?可眼下的自己,还有什么值得他如此费心的价值?她深吸了一口气来平复心绪。“令君就不怕留下我,我会继续对云罗不利?对君上不利?”她犹豫了一下才继续道:“令君就不怀疑……淳儿吗?”他笑起来,“淳儿不过一幼童,又能做得了什么?我也调查过你的身世并未做假……更何况……”他抓住了她的手,“以后我会看着你,好让你不用再做任何坏事。”他说他知道她做这些必定有自己的理由,或是为了报复兄长对她姐姐的辜负,或是与母亲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不重要……默默听着他的说辞,她忍不住问:“令君为我放弃了这样多,又想从浅雪这里得到什么呢?”她蹙起眉头,样子仿如山中警觉的幼狐。“说得也是,叛国,去家,失亲……我放弃的东西还真不少。”只见卓无涯满不在乎地笑着,忽然间神色一沉——“所以……我想要的,是浅雪你的一切。”说着他倾身向前,轻轻吻上她微凉的唇。她想要回碧珂山,虽然说那里会是首屈一指的追捕之地,但想到碧珂山地势崎岖道路错综复杂,是个极好的藏身处,卓无涯最终还是同意了。一路行经州府,他们看到了定国将军的丧报,却没有看到追捕他们的通缉,甚至定国将军的死因写的也是“暴病而亡”。虽然如此,也不能就此掉以轻心以为文重君放过了他们。“或许君上派了密探。”一日在饮马时,卓无涯看着溪水发了一会儿呆,忽然这样说。她点头附和,因为这件事也可算是宫闱秘辛,无论文重君或安若太后,想要以不惊动其他人的方法处置,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如果有一天和那些追捕他们的人狭路相逢,卓无涯又该怎么办?真的要为了她,大开杀戒,彻底与母亲和兄长决裂么?她不想问。于是只好假装不在意,专心将手中的苇叶编成一只活灵活现的蚂蚱放在树上,然后抬头看向远方。山色空蒙,碧珂山郁郁葱葱的南麓,已经看得见了。为了尽量躲避可能会有的追兵,他们走了一条少有人至的小路进山。这天夜里两人歇宿在一处崖壁上的天然山洞中,半夜时分她忽然惊醒,发现卓无涯并不在身边。他在洞口,而下方正隐隐可见火光。她起身走了过去,看见崖下是行进中的军队,正想发问,却被卓无涯点住了唇。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于是他们两人便保持着沉默,直到军队远去。“好像不是云罗的军队。”她率先发问。“是大夏……”弦月微光下,可见卓无涯的神色有一点凝重——碧珂山离边境尚有百里之遥,大夏的军队竟如此深入云罗。“莫非是要开战?”卓无涯摇了摇头:“若是要开战,军队该顺水阳江往西开往北原,眼下他们走的路沿途并无可供大军厮杀的平原,开战只是自缚手脚。”“那么……”“我想,他们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云罗,为接收云罗做准备。”“嗯?”她有些诧异,随后只听卓无涯笑了一声。“大夏对云罗志在必得……与大夏相比,云罗的军力根本不值一提,母后一直打算如果大夏来攻便交出玉玺开城投降,以保云罗百姓不受屠戮。只是叔父一直反对……如今她既下狠心杀了叔父,想必是与云罗的实权人物达成了协议。”他说着看向她,目光灼灼:“这些,母后都没对你说过么?”她默然片刻,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换了个问题:“太后的这些打算,君上可知道?”他摇头,“不清楚,但君上会答应的。几个兄弟中,君上的性格最像先帝,温文懦弱,他不愿征战,更何况现在叔父已死……浅雪?”他惊讶地出声,是因为她忽然凑到他面前去了。“你真是把什么都看得很明白呢。”轻抚着他的脸颊,她放柔了声音,“怪不得,九王爷说你留不得……要我一定杀了你。”卓无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抬手似乎想抓住她的手,但手方举到半空便软软垂下。“别怕,这不是鸩毒。”她的语调中,透着森森的寒意,就像初见时那样,仿佛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陌路。“对付你我用不着鸩毒,因为你总是太相信我了,不是么?”她俯身到他耳边,“可知太后为何一定要杀我?那是因为她知道,定国将军死后,我下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这是卓无涯在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带着能够撕裂心肺的疼痛,随后黑暗袭来,掩盖了一切痛苦与哀伤。数日之后,碧珂山的困龙涧。辰时,山间的岚依旧萦绕不去,架于深涧上唯一的吊桥有一半都隐没在白茫茫的雾气里,桥上铺着的木板也异样湿滑,如果有谁在这个时候踏上吊桥,总觉得向前再跨一步,就能进入腾云驾雾的神仙境地。幸好日头很快越过了山峰,雾气在阳光下渐渐消散殆尽。吊桥的东面,有着约十余人,为首的紫袍人,手中把玩着一只苇叶编成的蚂蚱。那是她沿途留下的记号。夏浅雪望向那人,躬身行礼,“参见王爷。”她的脚边,是依旧昏迷的卓无涯。7身着华贵紫袍的男子有着一副颀长挺拔的身材,面容亦是俊俏,只是可惜有一道伤痕自额头斜斜而下,划过左眼,破坏了面容的同时,泛白的左眼亦显示视力已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或许天妒良材,见不得有哪个凡人太过完美。“果然是云罗的靖疆令,浅雪你受累了。”男子看向她脚边的卓无涯,微微一笑。“幸不辱命。”她依旧欠身,微微低着头。“那么,现在替本王杀了他,用毒?用刀?或者就这么丢下去都行。”她抬起头,“王爷可还记得与浅雪的约定?”“哦,”男子应了一声,打了个脆指,身后的从人跑进树丛,不多时抬出了一只鸟笼。笼子很大,足以容人,不过此刻里面关着的是一只奇异的鸟。它的形态看起来像鹰,但周身都披着乌鸦般的黑羽,甚至连它的喙和足也是漆黑的。只有它的眼睛是红色,鲜艳得如同最上等的红珊瑚,又仿佛是刚从人体内流出的鲜血。它静静地停在笼中的横杆上,但边上的人看着它,都不自觉地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他们应该害怕——她这样想。因为那是鸩鸟中的王者,黑鸩。要想捕捉它,鸩者需要付出比性命更为贵重的代价,他们的生魂。每一只黑鸩只能为一个鸩者捕捉,鸩者得到它后便要将自己的一部分生魂寄于其体内,即可说与它分享自己的生命。如此,不离不弃,至死方休。而当一个鸩者将自己的黑鸩交予别人饲养,也就等于将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对方手中。她就曾经那么做。为报复那个辜负了姐姐的男人,让他国破家亡,她自荐于眼前的男子——大夏天子的第九子,并献上黑鸩,以示自己决不反叛的忠诚。而他将她推荐给长久以来共谋的安若太后,又暗中嘱咐她杀掉定国将军后还要除掉卓无涯,好助他兵不血刃的得到云罗。现在,该是他们两人都得到自己最终想要的,结束这场交易的时候了。九王爷一挥手,从人打开了金笼的门,黑鸩扑扇着翅膀从笼中走出来,转动着脖子左右望了一下,从人们纷纷后退,随后它展翅跃下了深涧。下一刻,比鹰隼更为迅捷的身姿自崖下冲出,直往天际而去。奇异的长鸣,在山间回荡。她目送黑鸩自由而去,轻轻叹息了一声,在昏迷的卓无涯身边蹲下身,伸出双手在他的上方轻轻搓动起来。有细小的的颗粒自她掌间泄下,日光照来,闪烁点点银光。卓无涯皱起了眉头,显得十分痛苦,只是始终不能醒来,而血色正从他脸上一点一点消失。最终,他紧抿的嘴张开了,挣扎的手脚也停止了动作,胸膛亦再看不到起伏。他的脸色,变成了微青的惨白。“漂亮。”桥的那一头,九王爷轻轻击掌,随后向身旁的从人使了个眼色,“去把尸体带过来。”“且慢。”她起身阻止,又行过一礼:“逝者已矣,靖疆令与浅雪也算有一段渊源,希望王爷能准许我将其妥为安葬,也算尽最后一点心意。”闻言,九王爷笑了起来,“渊源?浅雪你忒狠心,这卓无涯待你可说情深意重,却被你一句‘渊源’便一笔带过。”他目光转冷:“本王信不过你,所以本王要砍下他的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话音未落,数个从人已冲上了吊桥。而下一刻,她抽出了卓无涯腰间的唐刀,狠狠砍断了吊桥的绳索。有逃避不及的从人惨叫着掉了下去。九王爷冷笑了一声。她觉察到身后有人,回头一看,果然见有数人已自隐蔽处出来,正步步向自己逼近。横下一条心,她将卓无涯负到背上,然后走向了崖边。乌云蔽日,仿佛只是转瞬的功夫,山岚又起来了。“想置之死地而后生?”对面传来九王爷带着嘲讽的声音:“夏浅雪,可知本王要对付的人,上天入地也是逃不开的。”他这样说着,然后她看到在他的身后,不知何时从人又抬出了一只金笼,那里面——也有一只黑鸩。刚才他放走的,并不是她的黑鸩!也就是说她的生魂依然掌握在他手里……他早已料到她不会杀卓无涯。“哈……”一声轻笑自口中逸出。在感到身后有人袭来的同时,她前倾了身子——与卓无涯一同坠下了山涧。过了很久之后下方才传来轻微的水声,清楚地听到了动静,九王爷微挑剑眉,“愚蠢……”困龙涧的底部,是幽深冰冷的狭长水潭。虽然潭水削弱了下坠之势保全了她的性命,但因为长年不见阳光而冰冷刺骨的水还是让夏浅雪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过一次了。光是将卓无涯的身子推上岸,就好像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之后她又经历了几次落水才终于爬上了岸,赶紧从怀中取了药囊,颤抖着手解开取了解药放进嘴里嚼碎了喂给卓无涯。然后,用力搓着他的心口,看他每一点反应。四下里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是之前自吊桥上坠落的从人——撞到了山崖,入水时已经死了。潭水中染了血。忽然卓无涯动了一下,随后咳嗽起来。“无涯……”她大喜过望。虽然一切都是精心计划过的——能够呈现假死面貌的毒药,选择过的会面地点,但是总说人算不如天算,她不敢说有十成的把握。更何况,所谓关心则乱。卓无涯睁开了眼睛,脸色依旧惨白,但目光落在她身上后,眼神便渐渐从迷茫转成了锐利。她的手,下意识地缩了回来。此刻他会如何看她呢?凶残的刺客?无情的毒女?还是……“为何不告诉我……你的黑鸩在他手里。”“嗯?”一时之间,她没能反应过来他话中的意思。“刚才……我都听见了,那叫声我听过,是黑鸩……”卓无涯说着,扶着头勉力支起身来,目光却始终未离她身上:“你的生魂在他手里……设这样一个局,只是为了夺回生魂。浅雪,你从没想过要杀我,是不是?”有冰凉的水滴落到了手背上,她这才惊觉自己落了泪。该说什么好,是不是该诅咒这孽缘?是不是该后悔为什么要在初见的时候就对他动了心?是不是……只是没用,现在说什么都已太晚。而她,从未后悔自己动了心。下一刻,卓无涯将她拥进怀里。他们俩的身子都还那么冷,只有心口是暖的。他还带着些颤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浅雪,你这样做,是为了要永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别想骗我,我看得出来,你若非对我用了真心,我又怎会大意着了你的道……”话说到后来已带了点笑意,卓无涯似乎还觉得挺得意——她忍不住要觉得他是个笨人,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她偏偏中意了他。紧紧抱着他,恨不能这样就是一生一世过去。可是不行……她的黑鸩,还在九王爷的手里。她,命不长久……正在犹豫是该狠狠推开卓无涯,说些恩断义绝的谎话,就此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要就这么靠在他怀里,求取这最后的,哪怕短暂如秋叶旋落的温暖幸福——忽听得一声长鸣,巨大的黑影自上方落下,停落在潭边的尸体上。黑色的喙,啄食了死者的眼珠。她回过头去,与那对鲜红的圆眼对上时,她恍然明了。这竟是她的黑鸩。九王爷……“王爷,就这么算了?”心腹之人看着空空的金笼,神色疑惑:“不杀卓无涯,行么?”九王爷哼笑了一声:“云罗不日便是本王囊中之物,行与不行,还不是本王说了算!”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大费周章的——在接获卓无涯带着夏浅雪一同逃亡的消息时,他完全可以立刻派人截杀。可他却选择让夏浅雪将人带到碧珂山,双方当面交易。他想象得到她一定会耍诈。他只是想看看,那冷冰冰的毒女,能为一个“情”字做到怎样的地步?而夏浅雪的表现那么精彩,让他觉得很满意。所以这一次,就放过他们吧。后世,根据大夏史记所载:烈帝十一年,帝之九子诸山王统兵入云罗,云罗文重君献地奉玺,归我大夏。诸山王纳其地,于庶民秋毫无犯。云罗王族,后尽归隐深山,不知其踪。只有偶尔,在碧珂山中,还能听见黑鸩直达天际的长鸣,回荡于山谷,久久,不散。相关阅读:我已为你叛国,离家,失亲,现在能亲你一下吗?(上)作者简介橘文泠期刊作者微博:橘文泠原文名:满堂花客三千醉本文插画师:鸦青染。文中图片已获得插画师授权,若转发、使用,请咨询插画师鸦青染。点这里,让我知道你在看国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cd/4463.html
- 上一篇文章: 什么血型得什么病最健康的血型居然是h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