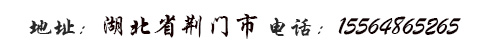毕安社父亲与军旅的爱恨情仇
|
我的父亲毕建堂。老人一生没照过几张相片,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他的仅存的容颜 父亲在他踏入91岁那一年,也就是年6月24日驾鹤西去,走完了他漫长而又辛劳的一生。如今12年过去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仍然折磨着我。有位作家说,只有做了父亲,才知道父亲一生的艰辛;失去了父亲,才知道父亲肩上养家糊口重担的沉重。回顾父亲的人生,让我对人世间许多事物有了醍醐灌顶般的感悟。 父亲生于兵荒马乱的年六月初三,从降生人世间的那天起,贫困与饥饿就和他的童年如影随形。民国十八年(年),靠天吃饭的陕西扶风县持续干旱,夏秋粮几乎绝收,加上莫名其妙的雪灾、蝗灾和瘟疫,饿死者遍地都是。为求生存,老家的大部分人弃家外逃,九岁的父亲跟随爷爷、奶奶和六爷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衣不遮体、居无定所、四处飘荡的讨饭之路。 父亲告诉我,他们在陇县固关一带逃荒时,六爷带他进到一家比较富裕的庭院里讨饭,主人不但没给吃的,还一顿叫骂。因为肚子实在饿得慌,年纪稍大一点的六爷趁人不备溜进灶房偷了一个馍,主人发现后提着棍子追了上来。逃跑中,六爷发现路边有一滩牛粪,灵机一动将馍馍塞进牛粪里跑开了。主人见状骂骂咧咧地回家了,六爷这才带着父亲返回,从牛粪中刨出并分吃了这个馍。9岁的父亲已经看尽了人间的眉高眼低。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邻省山西、河南。为救国图存,父亲参加了陕西军政部第25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毕梅轩任师长的陕西抗日游击师,开赴河南灵宝驻训(后部队改称第一战区第六游击纵队)。年初,父亲又奉命开赴山西,驻守晋南翼城、垣曲一带,隶属爱国将领赵寿山的国民革命军38军。 年夏,中条山战役打响,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战斗。由于兵力、兵器过于悬殊,最终导致战役失利,毕梅轩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被俘,父亲跟随毕梅轩的养子、营长毕长明突围后,跨过黄河撤退到河南卢氏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抗战胜利后,在毕长明的关照下,父亲在部队主要从事经商活动,用利润为部队购买给养、被装、骡马、日用品等军需物资。由于经商的需要,父亲的行动相对比较自由,经常往返于河南、陕西之间,其间还多次回到过家乡。年初,毕长明所在部队开赴四川,在外跑生意的父亲与其失去了联系,便自动脱离部队回到家乡。脱离部队时,父亲手上没有任何曾经当兵的凭据,特别是因为他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不敢讲出自己的经历,后来政治环境宽松了,父亲的战友却一个个过世了,没有人能证明他参加过抗战的经历,为此父亲常常懊悔不已。 我觉得,这段不黑不白的当兵经历不说也罢。不过也不可否认,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改变了人生,让他比渭北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农民多了些家国情怀,多了些土里扒食之外的生存技能。 父亲这段当兵经历,也给毕家引来了祸水。本县天度乡土匪王岁林得知父亲给部队做买卖,判断我家肯定有鸦片,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匪先是砸抢了隔壁国民党师长毕梅轩的家,又冲进我家绑架了爷爷,逼他交出大烟土。爷爷拼命挣脱逃出,被追上来的土匪开枪击伤大腿,再次抓住拖回后,土匪用扫帚沾上油,点着后在爷爷身上连戳带烧,致爷爷当场昏死。父亲返回家乡时,爷爷身上多处严重感染化脓,虽经大陈村医生陈广裕(音)全力医治,但最终不治身亡。 正是: 十年奔走乡愁切,百里归来家祸生。 仰面呼天天不语,低头告地地无声。 面对如此困境,作为长子的父亲,不得不放下在外游荡的心思,把仇恨与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与奶奶相依为命,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为了这个贫寒的家,父亲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顾不上,直到解放后才与母亲成婚,31岁时才有了我的大哥。这在早婚成风的农村是个特例。 扶风县法门寺古塔没有倒塌时的模样 记事时起,村民们都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而粮棉油则按家庭人口数量、挣取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那时,我们家是一个14口人的大家庭,叔父在外工作,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劳力,母亲、婶子既要参加劳动,还要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挣的工分少,年底生产队决算时经常是“短款户”。这种情况直到大哥、二哥(叔父长子)初中毕业,开始参加劳动后才有所改观。 父亲个头不高,身材偏瘦,咋看不像个出大力、流大汗的庄稼汉,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为了维持生计,父亲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泥土打交道,像犁地、磨地、施肥、播种、浇灌、收割这些活儿,父亲都是行家里手,像打胡基(农村盖房用的建材)、摞摞子(从地里收割回来的麦捆来不及碾打,需要先码放在麦场里)、挂粉条这些既要有体力,也要有技术的活儿,父亲从不贪闲畏苦,总希望挣的工分多一点,自留地的收成好一点,不让家人饿着、冻着。 可能是因为青年时期当兵走南闯北的缘故,父亲对经商有偏喜,被村里人称为“大能人”。合作社时期,父亲与人合作,把各家各户的油菜籽收来,在本村的油坊榨成油,再卖出去,赚取差价。为了多挣几个辛苦钱,他们买来两只用竹篾编的油笼子,装上近百斤食油后,两人轮换着用扁担挑去西安贩卖。 家乡距西安有里地,他们挑的是重担,一步三晃,满身大汗,肩头常磨出血来。这样走常常四五天时间才能到达。途中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讨水或在河道里用双手掬些水喝,累了就睡人家屋檐下。到了西安,油也不能很快卖出去,总要吆三喝四,讨价还价,费尽心力才能成交。一个来回要十天半个月,十分辛苦。但这比种庄稼的收入高出许多,父亲他们乐此不疲。 公社化后,长途贩运成了投机倒把,父亲往西安贩油的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可对于头脑灵活的父亲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在那个商品不丰富、物流不发达的年代,“集市”是农村地区易货贸易、商品流通的重要形式,精明的父亲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挣钱的新“门路”,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中介。 那时我已经成了父亲身后的一个“小尾巴”,人小嘴馋,每次跟随父亲去赶集总想着吃东西,一根麻花、一碗豆腐脑会让我高兴半天。可父亲老在牲口交易市场转悠,时不时会将右手伸进别人袖筒里,或在草帽、衣摆下捏摸着什么,嘴里还念叨着“这个百、这个十、这个元”之类的话。 出于好奇,趁着父亲蹲在地上抽烟的空当,我问:“爹,你们这是弄啥呢?” “捏价呢,帮别人说价呢。”顿了顿,父亲又微笑着对我说:“今天生意不错,等一会儿给我娃买碗羊肉泡。” 西北农民捏价的老照片 那时的一碗羊肉泡馍不到三毛钱,可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就是饕餮大餐了。后来注意到,每次成交后,买方或卖方会给父亲多则一两块、少则三五毛的钱,收益多少以成交价的高低而论。父亲这种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当时叫“经纪”,一般是由买卖双方都信任的人或当地声望比较好的人担任。 养猪是那时农家的一大经济支柱,一年的开销就指望卖猪娃(仔猪)、缴肥猪的钱了,而庄稼的基肥也要靠猪圈堆积,因此我们那儿家家都有一个厕所、猪舍、猪圈三位一体的后院,相当于农家的“小银行”。 我们家后院的猪圈比别家大,多时能养二三头猪。春夏季节,父亲每天收工的路上会顺便拔些青草,我们几个子女也会利用周末专门去地里拔草回来喂猪,到了秋冬季节,则把庄稼的秸秆或干草打碎,再添些麸皮,用潲水(刷锅水)搅拌后喂猪。猪娃养到8至10个月时,父亲拃量(张开大拇指和中指量东西)一下猪的长短、宽厚,估摸着有一百七八十斤了,再追加精饲料上几天膘,才送去公社的供销社上缴。家里养的猹(母猪)产猪娃的时候,父亲最上心,他要一遍遍去猪圈查看、照料,等猪娃长到三四十天了,再带到集市上卖掉,或留一两头健壮的猪娃自己育肥。平时,父亲也会从生产队指定取土的壕里拉些土回来,覆盖在猪粪上做基肥。 父亲还有一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就是杀猪宰羊,说不好听一点叫屠夫。过去在农村,男子结婚时,条件好的人家会杀上一头猪,以便把婚宴办得体面红火。冬季农闲时,人们嘴馋了,也会以“打平伙”(现在称集资或AA制)的形式买来一只羊,宰杀后在谁家煮熟后再分给各家享用。同时,各生产队都有养猪场,临近春节时,生产队会杀上几头猪,按人口或工分把肉分到各家各户。父亲看到了这个“商机”,学会了杀猪宰羊,方圆十几里内有宰杀的活儿都会请父亲去。尽管报酬可能只有几块钱,或是一两斤肉、半副下水,但在那个缺荤少肉的年代,这些东西增加了我家锅里“油水”,让村里其他孩子既羡慕又眼气。 父亲拼死拼活,终于让濒临破败的老毕家重现生机。庭院里儿女成行,匣子里有存钱,仓里有余粮,我们兄妹5人再也不为饿肚子发愁了。我上中学时,村里还有些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家除了能吃上玉米面粑粑(发糕)、金裹银馒头(一层白面和一层玉米面裹在一起蒸熟)、糁糁面(在玉米糁子快煮熟时加入适量面条),隔三差五还能吃上一碗漂着葱花的面条。每到这时,父亲皱纹纵横的清瘦的脸上会有一丝浅浅的满足。 在扶风高中读书时,住校生要从家里把面粉、玉米糁子背到学校,分别换成学校自制细粮、粗粮粮票。开饭时,再用粮票从灶上买来一碗包谷糁或一碗面条,每天还要5分钱的菜金。一碗包谷糁或一碗面条,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省钱,大部分学生都会利用周末的机会,从家里背些馒头或锅盔作为补充。家庭条件的好与差,从同学们背来的馒头或锅盔中便可略知一二。 多数同学背来的馒头或锅盔又黑又硬,特别是临近周末时便发霉难以下咽。可能是父母担心我面子上过不去,也可能是父母对我这个家里唯一的高中生的偏爱,每个礼拜回家,我总能背上一挎包白面锅盔,显得与众不同。已经知事的我明白,兜里的学费是父亲起早贪黑挣下的,背来的锅盔是父母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的,我在学校的体面和“虚荣”,全因身后站着辛勤劳作、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父母。 在我印象里,会挣钱、能挣钱的父亲从来不舍得给自己花钱。过去当兵时在外闯荡,父亲有着浓厚的“茶瘾”,可是他买的茶叶从来都是商店里最便宜的“处理品”,味道不够就熬着喝,水都没颜色了还舍不得倒。 父亲是知道穿戴的人,过去在外跑生意,长袍马褂、石头眼镜是标准装束。可是,自从当了农民,他没给自己扯过一尺洋布,从来都是一身黑土布对襟衣服,那些不甚好看的夹袄、棉袄,无一例外的是母亲自己纺线、织造、浆染、缝制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是,这些土里土气衣裳在父亲身上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让父亲显得体面。 父亲烟瘾大,一生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就是那个平时攥在手里,干活时别在腰上,空闲时含在嘴上的铜头、玛瑙嘴的旱烟锅。可是,为了省钱,他连火柴都舍不得买,用火镰打火点烟。 父亲对自己是想尽办法地“抠”,对儿女却是不遗余力地“惯”、倾尽全力地帮,每个儿女的事都在他未雨绸缪的计划中,安排得妥妥帖帖。年,我在西安谈了对象,父亲很高兴,雇车从扶风老家送来半车木料,供我打造家具。年初,弟弟结婚不久,家里花销不小,可是父亲竟然又塞给我一万块钱,说是其中的五千元是托在省城工作的大舅买奶牛的,另外五千元让我筹办婚礼。我当时是副连职干部,每月工资71元,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很是吃惊。但是打开纸包,看到这摞皱皱巴巴、散发着烟草味的钱币竟然有不少一元两元的,真不知道他这些钱攒了多少年。想到父亲的不易,不由得鼻尖发酸,湿了眼眶。这哪儿是钱呀,分明是父亲一生疼爱儿女的心血啊。 父亲晚年时腰弯背驼,不能下地了,还经常拿着镰刀到塄边、渠边割草,用背篓背回家剁碎后喂养猪羊。有年夏天,我回家探亲,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说他骑着自行车去邻村卖菜去了,我听了十分着急,追过去埋怨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骑自行车,你挣什么钱,出了事怎么办?” 父亲却说:“只有闲死的人,没有累死的牛。听说城里孩子上学可贵了,我能挣一毛是一毛,能帮一把是一把,不能让娃白叫爷么。” 父亲这话,叫当儿女的听了,扎心呀。 我们老家有一种习俗,儿女晚辈们要提前为老人准备棺材、寿衣,以便老人百年之后使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的寿材早已准备妥当,包裹得严严实实,架在我们家门房的房梁上。读初中时,奶奶还在世,父亲也就五十出头的年纪,他就托人从太白林业局买来一粗一细两根松木滚子(圆木)运回家,又请来解板匠人解成板材,一直码放在井房里。按理说,父亲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几个当儿子的应该早早为父母打造好棺材,但毕竟我在外工作多年,感觉家里放口棺材多少有点忌讳,这事就耽误下来了。想不到,父亲又买来棺材的挡木,请来匠人为自己和我母亲打造好棺材、上好了油漆,甚至连寿衣的布料也扯好了。 我知道后有些生气,就问父亲:“你是怕儿子不孝,今后‘百年’了把你用席片卷着埋了?” 父亲笑道:“你们哪个不是养儿养女,买房买车欠账一大堆?趁着自己能动,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年初,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急忙赶回老家。看见脸色蜡黄、卧病在床的父亲,着急地再三动员他去西安检查治疗,父亲坚决不去,还振振有词:“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已经73岁了,活不了几天了,我哪儿也不去。”好说歹说才将父亲接到西安解放军医院,经检查患有严重肝腹水。主管医生建议给父亲输几瓶人血白蛋白。医院药房工作的战友妻子帮忙,买来一瓶进口的人血白蛋白给父亲输上。 一天,他从护士口中得知他输的药一瓶近元后,铁青着脸对我吼道:“我不看病了,你把我送回去!” 我十分委屈:“带你来看病是有罪了?” “我是要死的人了,买那么贵的药干啥?” 我这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执意不来西安检查治疗,为什么现在又生这么大的气,他是怕花钱,怕给儿女增添负担。 我骗父亲说:“医院,你是军人直系亲属,看病用药是免费的,不用担心钱的事,医院治病。” 我还编理由吓唬他:“你不好好治病,医院声誉,组织上也会处理我。” 反复劝导下,医院治疗了一个疗程。这次住院加上后续的治疗,成功延续了父亲18年的生命时光。 父亲这辈子最为骄傲的,是我当兵,因为圆了他的家国梦。他虽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在民族危难时却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日战争,他也知道部队上出息人,所以,在大哥刚满18岁时候,父亲就要送大哥参军,可因为奶奶阻拦,大哥的从军梦半途而废,孝顺且无奈的父亲为此叹息了很长时间。 年底,我也满18岁了,当时中越边境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部队,之后又动员支持大哥,将我的两个侄子先后送到了部队。儿子、孙子当兵,让他少了儿孙绕膝的快乐,家里也少了壮劳力,年迈的老人不得不挑起屋里屋外忙碌的重担。 我穿上军装的第一张照片是在武威城里的东方红照相馆照的,这张照片我自己已经找不到了,老战友熊健却为我保存了43年 我与战友师军陪同56师老师长赵奋在兰州中山桥合影,我怀抱的小孩是老师长的孙女 年12月,我所在部队正在紧张地准备赴老山轮战。一天午饭后,军务处参谋李进会提着行李,带着父亲来到我的宿舍。猛地见到父亲出现在面前,我非常震惊:“爹,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也来看看我孙女儿。”说着,父亲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进我尚未满月的女儿襁褓里,算是给孙女的见面礼。 得知父亲还没有吃饭,正在伺候月婆的母亲便到厨房做饭去了,我爱人也急忙下床从厨房拿出一只碗,倒上开水送到父亲手上:“爸,你咋找到我们的?” 父亲得意地说:“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了”,说着指了指放在鸡蛋篮子上面的信封,又指着自己的嘴巴说:“鼻子下面有嘴呢,不知道就问人呗。” 原来,父亲听到我要上前线的消息,经历过战乱的父亲,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二话没说,提了一篮子鸡蛋和一包红糖就上路了。我老家离部队多里路,父亲乘长途客车多次中转,逢人就问,才找到我在临潼的驻地。当时我刚从56师调入集团军不久,军机关几乎没有人认识我。父亲就蹲在部队的大门外,进去出来的军人他必定一一问过,幸好碰到与我一起从56师调来的李参谋,否则可能连部队大门都进不了。 吃过饭,父亲说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满月的娃娃,要回家伺候。我知道侄女比我女儿大两天,母亲在临潼,父亲只能留在家里照顾侄女,便没有挽留。在家里,可能考虑母亲和媳妇在场,父亲没有说一句有关打仗的话题。在送父亲去临潼汽车站的路上,父亲才心情沉重地问起要打仗的事情。 为了让他宽心,我说:“爹,我都大了,你就不要操心了。” 父亲急了:“看你说的,你去打仗,当爹的咋能不操心呢?” 我赶紧解释:“我在军部,不在作战一线,肯定安全。” “毕梅轩是师长,那么大的官,中条山战役还不是被日本人抓了俘虏?”父亲用他的亲身经历强调着自己的观点。 我说:“现代战争不是你们当年拼刺刀的年代了,短兵相接的场景很少出现。” “你们就不去一线指挥,不去一线检查吗?” 父亲内行的发问,我无言以对。 好在我们父子二人一问一答来到临潼汽车站,我要去购票,才中止了这场答辩。 临别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军令如山倒。军人打仗天经地义,既然上去了,就不能丢人!” 我急忙应承:“爹,你放心,我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不会给咱老毕家丢脸。” 登车时,父亲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情绪,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哭腔中似有命令,又似有哀求地说:“娃,我要你平安回来!” 不等我说话,眼中噙着泪花的父亲,扭头登上了公交车。 望着车子远去,我心想,父亲又要经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了。 47集团军部队赴老山轮战资料图 远在千里之外当兵,最让我痛心的是未能在父母床前尽孝,想报恩没有机会,有机会了却因条件限制不能让父母满意。 6年的时候,我在青海部队任职,借道出差回家探望父母,父亲提出要我给家里盖房。我那时刚在西安买了一套安置房,手头有些紧,问能不能缓一缓。临别,父亲拦住了去路,说要跟我去青海。我以为父亲开玩笑,便笑着解释:“青海海拔那么高,年轻人都受不了,你去了咋行?”父亲拉着个脸,认真地说:“不跟你去青海,我往哪儿住呢?” 我明白,父亲这是变着法子说盖房的事呢。 7年春节回乡探亲,母亲当着几位来家里串门的扶风籍老领导的面数落我:“安社也不给家里盖个像样的房子,他爹年纪这么大了,哪天人不在了,不知道往哪儿放呢。” 母亲的话深深地剌痛了我。当天下午,我和弟弟便商定了盖房事宜。房子盖好一层时,我特意请假回去看了看。只见87岁高龄的父亲,顺着梯子爬上楼顶,一面给工人们发烟,一面喊着:“往高里盖,往高里盖!”高兴得像个孩子。 因为盖房,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给我提钱的事,也是我给父亲唯一的“贡献”。 父亲这辈子,为了支持我这个当了一辈子兵的儿子,嘴里抠,肚里省,夜里梦,白天想,操了多少心,洒了多少汗,掉了多少泪,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他冲我张口时,我竟然说缓缓。 这件事办得不漂亮,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痛。 晚年的父亲患有轻度的痴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有一次曾经连续三天滴水未进。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用了两粒安宫牛黄丸,父亲才清醒过来。一年之后,父亲的生命再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全力抢救,父亲终于醒了,而且十分清醒,他说没事了,让我放心回部队。我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以为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父亲,便放心地回到了西安。想不到第二天便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觉得即便是有一千个理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而这种对至爱亲人的愧疚永远无法弥补! 父亲出殡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来了不少。他们敬重父亲的勤劳和人品。父亲在世时,认识人多,又特别热心,为近百对年轻人牵线搭桥,成婚成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带着儿女在父亲的灵前长跪不起。这让我更加坚信了那句话:一个人生前的德行,是他死后的丰碑! 我的当过抗日老兵的农民父亲走了,如同沙漠中的一粒细沙被风吹散,可在我的眼里,他是一座值得仰视的高山。从此,我的生活少了一个依傍,人生寻途问路少了一位导师。悲兮!痛兮!长夜难眠忆父恩,纸船明烛照天烧。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愿我能成为父亲那样被人记住的人。 .8.8于陕西太白 作者简介:毕安社,陕西省扶风县召公镇人,年12月入伍,历任56师战士、排长、参谋、干事,47集团军干部处干事,期间参加云南老山轮战。后调入兰州军区干部部任干事、处长,0年调任装甲1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5年任青海省海北军分区政委,年退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高级摄影师,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第5、6届副主席,曾有多篇论文在军队、国家级刊物发表并获奖。摄影作品亦多次获奖,被誉为青海“普氏原羚”著名摄影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cd/10835.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们耳熟能详的纬度经度到底是怎么
- 下一篇文章: 2022新番观察十月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