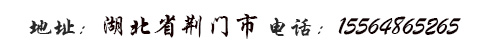庄如因
|
白点都是白癜风吗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429419.html 《庄如因》 日暮时他骑着摩托车沿平时的道路回家。 下班时候,河内市的老街上到处都是摩托车。人们戴着各色头盔,经过树荫路和盛满商铺的旧楼。从大约十几分钟前天气开始阴沉起来,暮色与渐厚的积雨云使古城区的破败感变得十分生动。他喜欢这样落满灰尘的底色,这使他觉得安全。 在棉行街中段的路口处,如果遇到红灯,他总得等一两分钟。这一次也一样在骑行的人群中等待。他想要把雨衣从身后的尾箱中拿出来,接下来还有一段路程,但看样子雨点快要掉落。 转头时,他看到在街角河粉店的露天座位上坐着的女子。 就此忘记了要拿雨衣。看了她一眼之后立即转回头,只继续认真看前方的信号灯和滚滚灰尘。眼望着灯牌上的数字在一秒一秒减少。二十七,二十六。他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注意到吸进的空气中有潮湿雨汽。二十,十九。他往河粉店反方向的左边瞥了一眼,又抬头看看低矮的云。十四,十三。排在前面的摩托车已经响起了预备行进的轰隆声。 十一,十,九。 终于又往河粉店门前的那个座位看去。店铺窄小的门面被漆为黄色,绑成一束的粗电线从遮雨棚下穿过。旁边是卖藤席的铺子,一卷一卷的藤席就立在她座位后方。 她穿着一件白色高领的长裙子,衣袖到手肘,是松软的面料。头发用木簪绾成髻。面容平和冷淡。坐在一个塑料椅子上,面前是方形的饭桌,摆着一个大碗,三四个碟子,热气上升至她的面前。有一些异乡人的疏远感。不像是越南人,像是来到河内的游客。秒数已经闪到七,仍在不偏不倚下降。 她却在无意识的远望中交汇了他的眼神,两个人隔着破旧街道和摩托车流对望。七。六。五。四。三。 她看到的是一个仍应算作年轻人的男子,穿着干净妥帖的布衫。没有戴头盔,轮廓是清秀的,骑在车上看到了她。她远远回赠一个自然的笑容。这时红灯变绿,车群依次发动前行。他回转过头,意识到对望使两个人建立起联系。 他感到紧张突如其来,从小腿到膝盖,再到大腿,再到腹部和胸口,有一种麻涩的感觉在缓慢上升。没有散去,而是如电波般停在体内。此时那波流已延伸至手臂与手指,他在波流的拍打中旋动油门,终于跟随上百个骑行的人穿过路口,就此离去。 他听到车辆轰鸣的声音聚在一起如乌云行进,将要散作破碎云絮去往四面八方的街。想到已作别店铺前坐着的陌生人,奇异的是酸涩波流微微延伸至眼鼻。 过了路口,在可以停车的路段,他去意未决地停下摩托车。下车站在一棵粗大的悬铃木旁,往回望。已经隔了宽阔道路和乌扑扑烟尘,隐约看到远处的人开始低下头吃河粉。风渐渐呼驰壮大,把旁边店铺的藤席吹倒几卷,店主人出来收拾,左右行走中挡住她的侧影。 他犹豫是否应当再站一会儿,等藤席都被整理好了,隔着道路或许还能再望到她的景象。但一潮一潮车辆往前,雷声从天的高处涌来,暮春大雨将至。他想这样站在道路的此端遥望彼端一个陌生人,或许实在没有要紧意义。 第二阵雷声到来前有骑摩托车的人从车潮中分流出来,摘下头盔喊他:阮寅医师,还没有回家吗?怎么停在这里? 是诊所旁银行里熟识的柜员,他落回真实地面,恍惚感消散。他微笑着招手回应,打开车尾杂物箱:我找一找雨衣。 银行员说:好的阮医师,我先走了。我没带雨衣,要紧快赶路。 他挥手道别,把雨衣拿在手里。再回头看去路那端的河粉店。藤席店铺前已有更多人在来回把席子往屋内搬,穿梭的人影中仅看到有她画面的窄长一角。 麻雀也已在树的枝干中找到躲避落雨的居所。他穿好雨衣,骑上车,继续在回家的道路行驶,雨点开始打在他的头顶与背上。他想,不知道她的座位有没有溅上雨水。如果她果然是游客,不知道什么时候将离开河内,不知道哪里是她的故乡。 十几分钟后到家,雨夜完全到来,路灯的灯盏像雨雾中栖宿枝上的黄鸟,羽毛被打湿,躲在浓重中是柔和一团。打开院门,右墙角的四棵老蔷薇枝叶被雨珠压弯,香味散落至地面上。他把摩托车推到车棚中停好,门廊的感应灯照出他的影子。脱下雨衣搭在栏杆上,开门,挂好钥匙,换鞋子,洗手,吹干头发。他换下在家穿的麻衫和长裤,去客厅把窗户大敞开。风带着碎雨珠子爽快地奔进来,他注意到窗外的草地边缘长出一些薄荷。 拿出手机时看到母亲的未接视频通话。重新拨回去,母亲正在她的茶馆中清理茶壶。离开父亲后,母亲慢慢在法国定居。这栋房子后来留给了他。那时医院实习,晚上睡在过大的卧室中总是不能够完全安稳。 母亲在巴黎的穆浮塔街不远买下独居公寓和一间茶馆,已经两年没回河内。这时是她所在时区的下午接近三点,母亲说两桌客人都在门口边的露台上,屋内空荡安静,她转动视频,给他看阳光怎样一天比一天照得更远。 母亲说:四月之后,白昼越来越长,上周的太阳才刚能照到第一个桌子,如今已经可以照到壁橱的橱脚。 他温和地回复母亲:是吗?我总在诊所里,并没有注意。现在河内下大雨。 寅,打上伞去院子和街上拍给我看好吗?我很久没看到下大雨时庭院和街上的样子了。 他顾恤母亲的乡愁,一边取伞一边说,“晚上去姨母的餐厅里吃饭吧?”母亲的母亲是河内人,她躯体里有一半的血液蕴含对越南的情谊。母亲的姐姐在巴黎十三区开一间越南餐馆。 旧城雨夜,院子里同时有门灯和街上路灯的光。他为母亲展示雨中的栏杆、草地、车棚、车棚边的蔷薇树、院门,继续前行。打开院门,屏幕照着街道、电线、电杆、邻居们的院墙,街道尽头的糕点铺子上挂着霓虹灯,霓彩在落雨中闪烁,梧桐树的花忽明忽暗。 母亲看上去是高兴的样子:好了寅,回去吧。晚上我就去你姨母那里吃饭。你也做些好吃的。她说着并整理好给客人的糕点要端到门外。她走在橱窗内的太阳底下,身上穿着灰青色奥黛。 阮寅站在门廊下挂断电话,风雨声混在一起奔呼。他看到回家时在摩托车上穿过的雨衣就在栏杆上挂着。他看到路灯在水雾中明亮极了,往前延伸,一直照耀河内古城的每一条街道。一个念头被推了出来。他重新感到麻涩的紧张感在从小腿往上升起直到胸腔。他穿上雨衣,把摩托车从车棚中再推了出来。 在大雨中驾驶,察觉到诗人们所描述的浪漫情绪并非无中生有。 凉风甚至使他微微发颤,他的身旁闪过一架又一架昏暗的灯火,水珠从电线落到行人的雨伞上,每一粒都璀璨如宝石。禅光湖,馆使寺,书街,考场街,到棉行街中段的路口。大雨如注。过红灯,停在漆成黄色门面的河粉店前。 河粉店仍然开着,两三个顾客坐在室内,遮雨棚下空着两个小小的露天座位。阮寅在其中一个位置上坐下,身后即是卖藤席的店铺。 他在坐下时感到自己身处其中的戏剧到达顶点,甚至因为过于美丽而有些悲壮。服务员把河粉和配菜端来摆在桌子上,碟子里的菜蔬红绿分明,碗上热气摇摇晃晃,很快消失到雨雾中。 他看着面前一波波车流穿梭,回想在暮色中自己是如何往这里张望。这是他从未敢有过的体会。 他想起她的发髻、衣袖,疏远和未知来处的熟悉,他们隔着轰鸣与灰尘的对望,他们的联系。 他的紧张、犹豫,红灯过后他停在悬铃木下又再次发动的摩托车。落雨前藤席铺来往人群中她身影的一角。 就像使他回忆往事,出现的都是某一些时刻的画面般,他几乎确信她远远坐在车流那端的样子会永远存留于他的记忆中,不会消失。他几乎确信如果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有人问他:以前你是什么样子?他在用语言回答时,想要描述的画面会包括远远看到她的大雨将落前的时刻。 他就在她坐过的座位上,把小米椒、九层塔、豆芽、洋葱丝全都倒进河粉汤里,挤好青柠汁,喝口热汤,看到夜色无尽,红灯前的车辆走走停停。 庄如因已经离开棉行街旁的河粉店,回到旅馆。 旅馆在还剑湖近旁。吃完汤粉,她沿着考场街走回去。售卖各种物品的杂货铺子在道路两边摆开,她经过残破的石板路和水泥路,灰扑扑的矮树,电线,骑摩托车的人们,门面窄小的咖啡馆。她慢慢地观看这座城市。 她在甘肃一家研究院的生态所做研究员,和同事来河内出差,工作行程到此日下午已经结束。同事订了傍晚的机票回国。如因想要在越南多停留两三日。 如因在路上碰到挑着担子卖百香果的人,买了两个,到旅馆时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房间在三楼,有老式台灯、一排面向街道的格子窗、布满瑕痕的木地板和黄色花鸟壁纸。书桌旁挂着河内老城百年前的复制照片。晚上八九点,窗外是古城的落雨,她处在温度适宜且安全的房间,腹部饱实,身体不觉得疲乏。坐在窗前看一会儿书。她带了一本诗集,读到的书页上这样写: 道别也没有痛泣过。 我在深夜里像矿石一般冷漠,只关心及饭食、星斗、睡眠。 唯有太阳才使我的同情之心稍微丰沛一些。 我把它当作至亲,我把太阳的光线当作我们亲缘的联结。 当我站在太阳下的土地上时,我即是饱满的。无需自责。 无需在饮宴时挂念除我之外所有人的喜悦。 无需在深夜挂念除睡眠之外所有心事的完结。 就像是描写她本身的诗句,像她的自白。她即是这样冷漠又诚实的人。心无旁骛,少有挂碍。她几乎完全自然与淳朴。 夜晚到来,至入睡的时刻,她把书本合上,在床铺中如石块般无情、坦白地睡去。清晨没有心事地苏醒,看到晨晖与茉莉花,感知世界的友善。她当然也是友善的,只是永远置身事外。她像天生的在悟之人。她以为比情感更广阔的事情在世上有无尽多,比如太阳的光照、川野的更迭。人生实短,应当尽量感知光明,不必拘泥于人与人的牵绊,情谊总应是光明和淡薄的。 而世事总不能圆满,每个人都在平等地进行一生课业。没有彻底的好事或坏事,美貌、财富、地位、聪颖,人们在尘俗中渴求的事物被信仰因果的人视为苦处。情缘、声色、芬芳、痴迷,人们以为是意义所在的事物被修行之人视作染污。如因得到的自在心境、诚实与少有留恋,由她对世情的冷漠换来。得到一项天赋,必然失去在没有这项天赋时可以获取的体会。 次日是晴朗天气。四月末的河内往往炎热起来,但因为前夜大雨,这一天凉风适宜。如因把头发扎起来,拉开窗帘,窗外的霞光几乎完全落往地面。她观看到很远之外霞色下的土屋,它们又矮又旧,像木柴般堆在平原尽处。楼下有十来岁的少女在挑着担子卖花,项上系起青色纱巾。 在旅店吃过早饭,轻便地向南或向北走,一整天都在河内停留。如因从推着自行车的街头商贩处买来一顶斗笠。去观看寺祠与市场,古树与民居。她经过一条长满梧桐树的道路,路口有挂着霓虹灯样式招牌的糕点铺子。梧桐花盛开,景象美丽,每一株梧桐树都端正并茂盛。 街道中段,一棵梧桐上飘起半片纸页。风雨剥蚀已久,纸上印刷的字迹已经斑污。如因走去把它揭下,发现纸页并不是被贴在树上的,而是由四个铁钉在树干上钉住。如因不情愿有钉子被扎在树干上,站定在清早的太阳底下尝试拔出钉子。钉得不深,拇指、食指和中指用一些力气就可以把它们撬出来。 忽然稍微手错,钉尖扎进食指指腹。 疼痛很快过去,变成细微持续的不适。如因看自己的手,伤口很小,略有些深,指腹上凝起一个血珠。钉子上有灰尘和锈迹。伤口应该要尽快得到清洗,沾满灰尘并生锈的钉子有带来破伤风的可能。背包里的水瓶却已被喝空,走来时也没有在邻近看到商店。 梧桐树旁边即是住家中的一户,铁门被漆成浅蓝色,从栅栏中看到一栋两层的房子和干净庭院,草木皆被照料得整齐舒展。应当会住着和善人家。 如因用左手按门铃,院子里房门打开,她看到面容谦和的主人家走出来。 如因隔着栅栏用英语询问:抱歉打扰您,我是过路的游客,不小心扎伤手指。请问可否借用清水冲洗伤口? 阮寅打开院门,看到他在昨日暮色时远望过的脸。 这是他没有在期望的重逢。却以为发生得不无道理。他的确觉得他与她在这一个世间已经建立起联系。在牢牢记住一段凝望的画面之后。一个人并不总是如此容易与另一个人建立起联系,长时间但未付出慎重情绪的相处,实则筛不出几个让人珍藏的画面。 他引她去庭院草地边的水池,打开水龙头示意她清洗。如因道谢,把斗笠摘下来放在旁边。他却用中文问她:你是中国人吗? 是。如因惊讶而怀有亲切地看他。 我也是中国人,苏州人。我的外祖母是河内人。他同如因说话时还带有一点南方口音。我能看看你的手指吗?他问。 她把扎伤的指腹给他看,在异乡遇到的同胞使她感到亲近。 如因补充说:是被生锈的钉子扎到,先清洗一下,不知道要不要去打破伤风针。 他转身回屋内拿出酒精和棉签放到水池边的石台上,示意如因在清水冲洗时用左手撑开伤口,确定水和氧气一直清洁到创口的最深处。而后他们在石台上坐下。 他有些拘谨:我帮你处理可以吗?我叫阮寅,是全科医生。刚开诊所第二年。 如因道谢。我叫庄如因,她说。 他拿起她的手指,两个人在太阳底下坐着,脚下长有茂硕的薄荷。他注意到梧桐花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感到世事似乎接近圆满。 他用酒精给她清洗伤口,做得细致妥帖。观察到创口偏深,于是询问她最近几年是否有补打过破伤风疫苗。 如因说:没有。只在小时候打过,这次还需要吗? 是。最好是。很快的,补一针类毒素就好。我可以在诊所里帮你打。 他推出摩托,骑车载她去往诊所。伤口很小,创面清洁,小时候产生过免疫,注射破伤风类毒素加强免疫即可,诊所对面的药店买得到。 他们沿着昨日他返家时的道路行进。不再是将落的阴云和大雨前气味、含混的黄昏沉霭,他们的脊背上落着正午时最清澈光线,两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躯身。如因扶着摩托车后座。街上行人往后奔去,老店铺林立,灰尘扬起掠过两人的衣襟。车流拥堵中他侧身看行道树,余光扫到她,白上衣,宽松的裤子,洁净的脸。很快回过头来,他的面前是阔大旧城。 再次经过棉行街中段路口的交通灯及他昨日停车远望的树下。是绿灯,不需要停顿,他载着她往前,与左侧黄色的河粉店擦肩而过。 他感到命运的奇妙馈赠,鼻腔内微微发酸。 阮寅把摩托车停在诊所门前,拿出钥匙去开卷闸门。卷闸拉起后有两扇玻璃门,四周是淡黄色干净的墙壁。他请她在等候区坐下,如因自然地坐到木椅上。太阳透过玻璃刚好照到她的鞋子。 开好处方后他们一起去对面的药店买针剂。两个人并肩过马路,路面不宽,从右边驶来汽车和摩托车。站在路边等车辆过完。他无法将心思集中在面前的景象上,眼睛在直视前方,在意的却是余光中左侧的身影。 如因心无杂念地观看街道。等待车流结束,与阮寅一同走进药房。听到他用越南语与药师对话。这种语言说起来经常需要拉长音调和转顿,但听到他在讲述时并不拖沓,语调清正。药师从第二排柜子中取来针剂。 他将药盒上的英文指给如因看,以告知她那是准确的药物。她直视阮寅的目光,向他道谢,一边从背包中取出五十万越南盾的纸币,递给柜子那边的药师。她微笑着这么做,脸上有感激神情。阮寅却局促起来,在这一刻他像站在心上人面前的少年一般厌恶任何涉及钱币的动作。他希望她什么都不要管,尽由他料理她的创口。他不适应这样的关系。 回到诊所,他们一起去另外一间诊疗室。干净的房间,器具泛着光,屋角摆有一盆鹤望兰。 打在手臂吗?如因问。 对。他重新去洗一遍手。拿起针管时觉得心安定下来。 如因把左边的衣袖拢到肩膀处,针剂打完,没有感到不适。她礼貌地朝阮寅医生道谢,感激他的帮助与友善。两个人走回外间的等候区,并肩坐在木椅子上。太阳此时已照至他们的膝盖。他注意到光线的移动,想起昨夜母亲电话中提起的白昼在变长。他看到房间中光明极了,像是完全被阳光充满。 你说你是来河内的游客。 是,阮医生。我前天来出差,昨天下午差事结束,同事们已经回去。我想留在河内看一看。 明天就走了吗? 明天去下龙湾,坐客车去。后天重新回来河内。后天傍晚从河内的机场回国。 他没有再说话,门外街道上传来汽车轰鸣的声音。他想起的是自己之前在医学院走廊里独自坐着或行走的景象。他习惯独自一人,与他人关系的处理总是让他不够放松。但此时却对与她即将发生的离别产生悲伤感想。 如因说:你在苏州生活过吗? 小学和中学都在苏州,大学开始就不在了。现在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回去。 他低下头又抬起头:一起去吃午饭吗? 如因回答:不了,我准备回去旅馆。阮医生,多谢你。我把地址和联系方式写给你,或许以后有机会再见。 她拿出记事本,写好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撕下纸页双手递给他。他看到上面写着的她的名字,目光在字迹上停留。 如因说:阮医生,多谢你。我要走了。 两个人都站起身来,他拉开玻璃门。她微微躬身致谢,挥手道别。对她来说这是亲切但简单的相遇,不必怀有留恋。 如因离开后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午后的老街稍微安静了一些,她背影的颜色完全融入周遭。阮寅一直站在诊所门前,看到她经过旁边的银行、早点铺子,再远一些的咖啡露台、饭馆、服装店,再远一些的旅行社、花店、居民楼。她在人群中越来越远。语言的混响与光斑的跳动将她慢慢掩盖。他看到在这条街的尽头,她似乎是停下观看了一株古榕树,没有回头张望一次。又转过一个弯,她已经消失不见。 阮寅走回诊所,坐回到刚刚的木椅子上,阳光完全将他包裹。手、脚、脸与脖颈都被晒热,腹内却有发凉的坠感,像做错一件大事。 独自思想片刻,他重新下定决心。锁门、骑车,往她走远的方向追赶。在路的尽头转弯,继续向前,远远看到她正在一个饮品摊前买水。等他骑车赶上时,如因正站在另一棵榕树下喝水。他把摩托车停在榕树边,走去如因近旁。 她惊讶于看到他。还没有说话,阮寅站在树荫中问她:明天坐车去下龙,我一起去,可以吗? 问完觉得手足无措。他实在不适应这样的情境。他解释说: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下龙湾。这个季节很好,应当去看一看海,明天我也休假。 如因至此完全明白他的好感。他是很好的人,有庄重的品性和善良的禀赋,并且温和,并且英俊。 如因说:阮医生,我从不信任恋爱的发生。 她以为自己过于直接,但他似乎舒展了一些。 为什么? 我一向为人疏远,内里冷漠,难以与别人建立起亲近关系。如因说。有贪求和渴欲的男女情爱是烦恼的来源。我只情愿与他人是光明的情谊。 榕树根须垂下三四根在两个人之间,行人穿梭。完全坦诚之后,他反而适应这样的情境。 如果我赞同你说的,明天坐车去下龙,我能一起吗? 约定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在美亭车站前见面。走下出租车后,如因远远看到他站在广场一角的晨霭中,淡灰色高瘦的轮廓,手中拿着她昨日遗落在庭院中的斗笠。阮寅将买好的车票递给她,两张略厚的纸片,盖着红色印章。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一刻钟。站在广场一角等待,看到红日初升,旅人慢慢变多。 班车是流水式编排,他们进站后刚好有立即要出发的车辆,剩余后排两个座位。旧巴士,装着三十几个乘客,像一座缩小的可以移动的河内老城,破旧但坚固,越南人与游人夹杂一起,行进的汽车声中听得到越南语、法语和中文的对话。怀抱幼童的少妇坐在他们前排,幼童在颠簸中入睡,他发觉幼童与如因有相似神情,是完全自然及不在意聚散。 三个半小时的行程,如因坐在他右侧的窗边,两人很少说话。他在如因背包的外侧看到一本诗集,向她借来阅读,翻到的一页他读到: 我又何尝不是需要太阳眷顾的稚子? 我又何尝不是手无寸铁地站在千百年的中央? 当我如白云般游荡, 我又何尝不是在为聚散而戚伤? 当我终于如丘野之风般自由, 我就再也无需自责。 无需在饮宴时挂念除我之外所有人的喜悦。 无需在深夜,挂念除星斗之外所有心事的完结。 如因闭起眼睛,破损的窗帘垂至她肩膀。她没有睡着,但她有纯粹地专注于当下自身想法的态度。她很容易摒弃杂念,思虑稳定不飘荡。这是她的长处。现代社会的信息量总是很大,如丛林枝叶般垂下覆盖生活其中的人群。人们却习惯了要被层叠枝叶包围,仿佛那是安全感的来源。借助传达信息的通讯工具,同样包括书本、音乐、艺术馆、圆桌会。饱满的与非饱满的,紧要的与非紧要的,直透内心的与浮于表面的,使人安宁的与使人焦躁的,各种讯息如各种树木,在人们周围飞速生长。包围得越来越紧,越来越被制作出美好形状。带来时间未被浪费的安全感。带来仍在上进的安全感。带来参与思考的安全感。由此人们愈渐害怕走入旷野:完全空旷,无枝可依;时间飞快向后并由此引起大风,必须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才能在旷野的风中站定。 这样的旷野有时会在深夜无法入睡时来临。人们沉入黑暗中,眼睛看不到讯息的枝叶,耳朵听不到抚慰的声音,睡意尚未到来,被迫观看自己的内心。悔恨、妄想、悲戚、烦怨、焦虑、痴迷,平素被枝叶包围而未得以照见的内心此时清晰如身在旷野。无情的人才能在旷野的风中站定。 这是阮寅难以做到的事情。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必须借助音乐或广播才能入睡。每日的生活中,必须在确切地做着某件事,学习、运动、工作、观赏风景或其他。独处时一定在阅读或学习知识,或做体力劳动。从少年时至今接近二十年,他从来没有一次在旷野久立,使内心被完全照见,接受大风吹打。他总是游荡至畏惧回忆的时刻。 公共汽车摇摇晃晃,阮寅看到如因合着眼睛,洁净、无挂碍地坐在他的旁边。她的存在似乎在给予他以前未曾拥有过的勇气。而汽车窗帘的缝隙里一座接一座香蕉园在向后退去。青翠的,芬芳的,正一并到来。 九岁时阮寅的父母亲居住河内,在懒翁街开一家中药馆,每年仅回苏州一次。他与祖父、祖母同住在太湖边的村子里。他是村里小学被喜爱的学生,安静的男童,有乌黑清亮的眼睛。学校门口的河水经过祖母家住所前再流往池塘。早晨他沿着河水去上学,傍晚排队走回家,天上总是挂有淡淡一枚白月痕。祖母常说,啥格辰光最好?上班葛上班,到学堂葛到学堂,一家门闹热吃饭,噶好辰光哉,太平点罢。 暑假到来的前一天,放学回家,看到门厅里有陌生长辈坐着正同祖父说话。祖父招手喊他,寅囝来哉,哀个是后巷邻家伯伯,二十七八年朆回乡哉。 后巷邻家的院子一直是空着的,孩童第一次见到这个伯伯,后来知道他早年得到一个契机远走他乡,至都市中安家。这是离乡多年后第一次回来,上了些年纪,积累下资财,算是衣锦还乡。要回来看看老屋是否需要修整。 祖父喊寅囝去端杨梅来给客人吃。孩童把书包放在格窗前的桌子上,端来杨梅递到陌生长辈的面前。听到他说“上几年级了?好孩子。”他接过盘子,手掌覆在孩童的手上。 暑假开始的第二天,祖父祖母在果园劳作,桃子的采摘季即将到来。孩童独自在家写功课。从小开始他便习惯先将要做的功课写完,而后才开始玩耍。院门是敞开的,村中诸事安泰,人们只有入夜才会闭起大门。他看到前日来做过客的后巷邻家伯伯走了进来,手中提着一兜瓜果。 “寅寅,祖父祖母不在家吗?拿葡萄和脆瓜来给你们吃。” “他们去果园了。” “寅寅在写作业吗?我看看。”他走近,坐在孩童写字的椅子上,把孩童拉往身边:“寅寅过来,坐旁边来。” 孩童不懂得如何躲避,甚至不知道躲避的意义。品性纯善的孩童对大人完全信任。他听从大人的话,以为世界上存在全都是好意。 中年人反抱着孩童在怀里,一页一页翻看纸上写的题目。天气炎热,紧挨的躯体使孩童感到不适,尝试从椅子上滑下来,再次被揽紧。听到他说:寅寅,作业做得好。 祖父和祖母提着筐走进院子,他放开揽着的孩童,迎出门厅:听寅寅说唔笃去果园了?我到镇上有事,买了些脆瓜一起来吃。 谢谢内,肚皮饿哉?到伲屋里巷来吃饭来哉?祖母笑着问他。 晚上吃饭时祖父与祖母絮絮讨论,说一别二十七八年,后巷邻居家伯伯已几不再有乡音。又说明天让寅囝送些咸鸭蛋给他去,人家不几天就走,要好好待人,礼节有来有往。 次日清晨,祖父、祖母又一早去往果园,叮嘱寅囝做功课休息时把咸鸭蛋送去给后巷邻居。孩童提着一个布袋,敲打后巷邻居大门。 中年人打开黑色大门,神色混沌像欲念发生时。他接过布袋,顺手把大门关紧。 “寅寅来,屋里看书来。” 孩童不安地想要往外走,却被拉住手臂。院落久未有人居住,杂草被胡乱拔起堆在墙角,白色的土块从外墙剥落。四处都是污暗底色,四处都是焦躁慌张。 “寅寅不要怕。我们屋里看书去。” 如因拉开车窗帘布,上午九点的清亮阳光落在她与阮寅的脸上。她朝阮寅微笑,光明,稳定,毫无心事。两个人衣襟的一角因为车辆摇晃而碰到一起,都是白色布料,阮寅的衬衫,如因的衣裙。干净的白,落满阳光的白。阮寅感到光明像可以流动一般,注而不竭地从如因身上倾泻到他的躯体与精神中。他因此也得以是光明的。而且光明将永存。 他忽然很想告诉如因他的欢喜。却说不出口。车辆从平坦大道进入一段亟需修整的路段,路面坑洼不平,行驶颠簸。光斑在两个人的身上来来回回。他侧过头望着如因的脸。他说:如因,你手受伤的前一个晚上,我在棉行街看到你。 如因惊讶地笑起来,是吗? 是的,我看到你。你在路边的座位上吃河粉。但红灯很快结束,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 如因至此想起她那时隔着车流遥遥与摩托车上的人短暂对视。 骑车的人是你,她自然地微笑说,第二天你认出我了是吗? 是的,如因。第二天我认出你了。 是的,如因。我猜想这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必然相遇的连结。 到达下龙市。刚刚正午,海边的城市到处飘满极干净海风。两个人都没有行李,只各自背着双肩包往旅店去,路上经过一段长长的坡路。旅店是一栋北越典型的窄型建筑,六层楼房,正面大约只有六七米宽,每层都有两个窗户,两座连接窗户的小露台。进入大门之后是厅堂,纵深很长,最尽头是四方形的小庭院。他看到庭院边种植了几株芭蕉。 来到前台边,他问:请问今晚还有空余的房间吗? 在前台工作的青年人查看后很快回答:有的,四楼还余有一间。可以现在帮您办理手续。 谢谢你,麻烦了。他递给青年人证件。 阮寅的入住手续办理好之后,如因拿出她的护照。青年人很快找到如因之前预订的房间:也是在四楼,今天入住,明天结束。您可以去尽头的庭院旁边乘坐电梯。明天的早饭也在院子里。 他们去各自的房间里稍作休憩。打开房门后,他看到阳光透进来。这并不是华丽的旅店,房间内仅有床、桌椅、简单用具。但有很好的朝向和露台。如因把窗户尽皆敞开,走到露台上。旅店已经处于高坡,又在四楼,因而能直望到很远处的景色。阮寅也在这时来到他房间的露台,看到相隔两层栏杆的如因。 此时阳光与风的包裹使他如同已抛开诸悔恨、妄想、悲戚、烦怨、焦虑、痴迷。使他内心晴朗并安全,使他在旷野中倍感安全地站定,心无旁骛。 他鲜少有这样的感受。即使在他长大成年之后,他亦时常未知缘由地感到不安。 中年人拉住孩童往暗屋中走去的早晨。紧闭的大门,远在异乡的父亲与母亲,羞辱的动作,拉扯的衣衫,哭泣与疼痛,憎恶与惶茫。门前的流水,新熟的桃园,停留湖畔的雁鸟,苍老和善的家人。 大门打开前,中年人已按住孩童洗净了身体,也已整理平整孩童的衣衫。中年人把孩童送回家中,忽而恐吓,忽而作可亲状。他讨好地笑着说: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又换上凶戾神情:你要是同别人说出去,你就毁了。你的一生都会毁掉。 中年人在当日下午乘车离开村子。 清白的孩童躲在灶房中,一边烧火煮水,一边默默流泪。 他必须让自己烧火煮水。在窄小的灶房里,火苗跳动着散发光热的时候,孩童得到被保护的感想。他必须让自己不停止地拨动火焰、倒入和倒出白水、掰断细柴、把柴火垒成角落中的矮垛。他的身体在做着另外一件与光和热相关的事,他就感到被保护。 似是很长时间已去,祖母背着一筐桃子、祖父一辆独轮车,两人回到家中。祖母去灶房看到正在烧水的孩童,摸着他的头发,拍打他的脊背。 寅囝吃桃子来哉。祖母笑着说。忽而发觉孩童的眼眶红肿,祖母慌问,寅囝? 清白的孩童扬起脸,泪痕在火光的照耀下几不可见。他嗓音平静:阿婆,烧一上午火,烟熏噶难受哉。 祖母把他抱进怀中拍打。寅囝,做仔葛上半日活计,阿婆葛好寅囝。 祖父去清洗桃子,这一季的蜜桃甜美丰盛。日头照到院子里,孩童烧满热水的六把保温瓶整齐地摆在石台上。 祖父说:寅囝噶勤快哉。今朝好天气,亦要再过脱一年,再有哀场长葛一段好天气哉。 下龙市布满民居和云絮的高坡上,阮寅隔着两层栏杆询问如因:下午原本有打算去到哪里吗? 他看到如因转过来的脸上只是寻常光线,却完全打动他。如同一块贫瘠的土壤恰好适合一株植物,那株植物就在这些砂石的缝隙中终于舒展开根系,得到抚慰与光明。 如因回答:没有特别规划,原本只打算在本地的街巷中走走。明天一早订了座位去乘船看海。阮医生,昨晚我在河内时帮你补订了一个船上的座位。 要吃午饭了,如因,我们走去坡下吧? 两个人并肩去往旧城中心,相隔大约一米的距离,不亲近也不疏远。很少说话。阮寅放松和安全地舒展开他的根系,沉默地结出叶子。他观看那些叶片:平整、碧绿、脉络清正,散发着干净平和的芬芳。 他们在一条窄街的河粉店前坐下来,面前是整片木头切成的长桌。他们相对而坐。街道尽头是依着沙滩的一条宽路,路那边有一座游乐场,高音量的下龙湾宣传片在游乐场旁立起的屏幕上循环播放。宣传片选用的音乐有优美旋律,从街道尽头飘到他们的饭桌前。 而后他们去近旁的市场。香料、鲜鱼、蔬果、器物,都是热闹的。如因买了一小袋香料,装进背包里。她说,等我明天回甘肃后,可以在饭菜中试一试。 阮寅说:如果你喜欢,就告诉我,我从河内寄去给你。 如因微笑着摇摇头。 暮色初降时他们来到邻海的越南餐馆,吃了一些简单饭菜。海岸边有一条灯火通明的商业街,路边紧挨着到处都是酒馆、小吃摊、纪念品店。游人们在各个摊位上买吃的,有水果,北越的点心和炸螃蟹。如因去买三色冻。而后两个人在一处露天座位上坐下,身旁到处是升腾的烟气。 阮寅喝一种当地的淡酒,颜色清澈,有少许薄荷的气味。 他在中学时第一次品尝酒精。他成绩好,初中结束后升至市里一座有声誉的中学。那时父母在河内的药店已开至第三家,经济越来越好,虽然相隔很远,见面也少,但尽量给他丰渥的生活。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个周末搭校车回去太湖边的祖父母家。 他成为沉默的少年人。他对自己的举止与思想都近乎苛刻。他必须时刻端正、规矩、庄重,严格地遵循每一条他能够看得见的规则条例。在行为举止与学业上,他是老师们能够想得到的最好的示例。而在他自己的评价体系中,他也必须是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典范。 宿舍中的男孩们很快熟悉起来,甚至邻铺成为了他的朋友。两个人个性迥异却意外相合。邻铺与他的床头相对挨着,有一天晚上熄灯之后,男孩从对面探过头来,递给他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是未开封的一小瓶白酒。男孩良泉以没有发出实声的耳语在黑暗中同他说:你尝一尝,阮寅,你喝过酒吗? 没有,我不喝,你收起来吧。 你尝一小口,良泉诚恳地说,没有什么坏处的,一会儿你就睡着了。 你从哪里买的? 我上个周末偷偷从家里带来的。良泉说:阮寅,你太板板正正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阮寅察觉到男孩隐藏于这一举动背后的好意,他接过酒瓶,把头埋进被子中,轻轻拧开瓶盖。他抿了一小口,辛辣的酒精味道涌入鼻腔,像完成了某种仪式。他把酒瓶递回给良泉。 良泉将酒瓶收好,坦白而赤诚:阮寅,你想让自己毫无瑕疵,我以为你太辛苦了。我有时想,你是在害怕什么呢?一些瑕疵毁灭不了你的人生。你应该放松一点。 他平躺好。他已不再是九岁的幼童。他已是笔直挺拔的少年人。他学习了很多知识,长大至羽翼丰满。他当然知道只要他足够坚韧,或者冷漠至完全遗忘,那么那些曾经使他无比恐惧的话语就会变得可笑。只要他冷漠至完全遗忘,那个羞辱的早晨或许可以在他的生命中不复存在。但他无法忘记作为一个经历暴行后的孩童,听到“你的一生都会毁掉”这样的语言后,浑身颤栗的恐惧感。 “一生”对孩童来说太过宏大。“毁掉”对孩童来说太过绝望。 他几乎已经封锁了对这些话语的记忆。他是秉性敏感的人,他想如果对自己禁止任何非道德的行为、任何谎言、任何恶习、任何与他人的亲密关系,那么他就会有坚如磐石的铠甲来抵御记忆中浑身颤栗的恐惧。 男孩良泉也躺回了自己的床铺。正直的男孩微妙感知到朋友的脆弱之处,想要尝试给予开解。 他感激良泉的尝试。已有很久他未曾体会到朋友或伙伴之间的情谊。这一个周末他搭校车回祖父母家,像往常一般在傍晚的庭院中与祖父母围绕木桌吃饭。饭桌上有油面筋塞肉与蒸白鱼,还有祖母做的赤豆方糕。他同祖母说想带几块方糕回学校给同宿舍的朋友。 祖母高兴地去找盒子:要弗明朝新做些,寅囝葛朋友哉。 祖父也笑着说:搿倷齐巧好露一手哉啘。 祖父与祖母继续在饭桌上闲聊,说起街坊们的讨论,后巷邻居家早年间移居外地的男人,听说近些天得了急症身亡。 祖母叹道:弗就是到过唔笃屋里来葛男葛么? 欸,长远哉。 他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一些禁锢在缓缓裂开。 如因吃完一盏三色冻,也去买来了一杯当地淡酒。两个人在海边的露天摊位上面对面说话。 我想起一位很好的朋友,在中学时我们相识,如今已经七八年未再见面。 如因说:为何不邀请他来河内游玩呢?不必担心未曾相见的时间。人与人的相处是由气息相契的,有些人在相处中始终感觉不到舒适与自然,是因为气息并不契合。而假如找到契合的朋友,时隔多年也仍将感到自然。气息就像相貌或体态,大多源于天生,所以找到契合的朋友并不容易。 气息完全契合的两个人会相互吸引吗? 如因说:会。 气息有好与坏的分别吗? 如因说:我不这样以为。麦子是我们的食物,稗草是鸟雀与羔羊的食物。美玉被称赞为美,石头和土坷被称赞为坚固与肥沃。 他们喝完淡酒,在灯火月色中走回高坡上的旅店。很快各自入眠。阮寅感到自己多年以来第一次如此安稳地入睡,他多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借助音乐或广播来填满入睡前的宁寂黑暗。此夜没有任何生于寂静之中的杂念。他看到旷野中满是光明。他知道这是如因就在隔壁的缘故。 祖父母相继逝去之后,他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依恋的情绪。包括对他的母亲。随着年岁渐长,他更多是怜爱他的母亲。遑论对女子的依恋或爱慕。 读书时偶尔对异性产生的微小火花总能被他以最快的速度熄灭。他端正、冷淡,由此引来愈多倾慕的目光。他冷冰冰地不予回望。仿佛那是他不应当触及的领域,仿佛吸引与被吸引是完全丑陋的,理应被他禁止。 直至此夜他想:依恋或爱慕,吸引与被吸引,这些情绪并不是丑陋的。他不再对此感到厌恶。 清晨如因在露台上喝茶。是如因自己在甘肃晒的炒苦菜茶,这次到河内出差带来一小盒。阮寅也已洗漱好,换上干净的衣衫,来到露台上。问候过后,如因隔着栏杆递给他另一个盛满茶水的杯子。茶杯是旅店里自配的白色粗瓷杯,圆形阔口,稍显陈旧。如因把它们洗净、晾干,喝苦菜茶时如有故乡的风吹过。如因品尝茶水或菜蔬时并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anxueliu.com/dxlcd/6909.html
- 上一篇文章: 拼团丨正版敦煌年礼
- 下一篇文章: ,敦煌年礼,今日首发